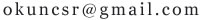一、“回目”之来源
“回目”的直接来源可追溯到宋元话本。在宋元话本的几大类中,有一类被称之为讲史话本,其基本特点之一是篇幅蔓长,说话艺人在讲这些故事时,并非一、两个单位时间可以讲完,只好逐日分段演讲,这就无形中将这些长篇故事分成了几十乃至几百个段落。为了便于说话艺人讲述和听书人的记忆,也为了使某些精彩的片断更为引人注目,这些话本在出版的时候往往根据故事内容分节立目。这种分节立目的方式,就是回目的雏形。
现存的宋元讲史话本共有十种左右,其分节立目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上图下文,如元刊本《全相平话五种》每一页上栏的图中都有标题,而下栏的文字中亦有以黑地“阴文”标目者,覆盖在相关处的“阳文”之上。例如《全相平话五种》之《三国志平话》中,就有“三战吕布”、“关公刺颜良”、“三谒诸葛”、“赵云抱太子”、“张飞拒水断桥”、“黄忠斩夏侯渊”、“诸葛七擒孟获”、“军师六出歧山”等数十条“阴文”标目,表示精彩的故事段落。《乐毅图齐平话》中亦有“孟子至齐”、“燕国立昭王”等数十条这样的阴文标目。另一种情况是在全书的卷首刊有目录。如士礼居刻本《宣和遗事》书首就有从“历代君王荒淫之失”到“秦桧定都临安”共293条目录。再如董康诵芬室影刻本《景宋残本五代史平话》中除《梁史平话》目录缺佚外,其他四种均书首有目。《唐史平话》有从“论沙陀本末”到“废帝自焚死”计107条目录,《晋史平话》有从“敬瑭割十六州赂契丹”到“契丹主监重贵还本国”计62条目录,《汉史平话》有从“刘知远本沙陀部属”到“推戴郭威为帝”共87条目录,《周史平话》有从“郭威家世业农”到“赵太祖改国号为宋”共94条目录。
一般说来,上述两种情况并不重复出现。也就是说,“阴文”标目者,只随正文标出,在书首却无目录;反之,书首有目录者,正文部分又无“阴文”覆压“阳文”标目。但无论如何,这两种“标目”的情况,正是后世章回小说“回目”之滥觞,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之为“准回目”。
除宋元话本而外,元代杂剧的“题目正名”也给章回小说“回目”的形成以极大的影响。以上所述的阴文标目或书首目录,均为参差不齐的不规则单句作目,只是标明故事大概而已,并非“美文”。而元代杂剧的题目正名却受到骈文和律诗的影响,全是两两相对的偶句,且读起来铿锵作鸣、琅琅上口。如元刊本《看钱奴买冤家债主》题目正名云:“疏财汉典孝子顺孙,看财奴买冤家债主。”再如元刊本《散家财天赐老生儿》题目正名云:“主家妻从夫别父母,卧冰儿祭祖发家私;指绝地死劝糟糠妇,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无论是两句还是四句,都对仗工稳,堪称“美文”。象这样的题目正名,还有元刊本《尉迟恭三夺槊》、《汉高皇濯足气英布》、《风月紫云亭》、《公孙汗衫记》、《薛仁贵衣锦还乡》、《东窗事犯》、《霍光鬼谏》、《严子陵七里滩》、《辅成王周公摄政》、《陈季卿悟道竹叶舟》、《张千替杀妻》等。当然,也有少量对仗不太工稳者,如元刊本《诈妮子调风月》的题目正名:“双莺燕暗争春,诈妮子调风月。”如元刊本《好酒赵元遇上皇》的题目正名:“丈人丈母狠心肠,司公倚势要红妆;雪里公人大报冤,好酒赵元遇上皇。”但无论如何,这些题目正名较之宋元话本的阴文标目或书首目录总要漂亮得多。这些对仗工稳的题目正名,给章回小说的“回目”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二、“回目”的演变
最早的章回小说的回目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实际上是无从说清的。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成书最早的几部章回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等,均无元末或明初的版本。它们的最早出版时间,据目前所知,分别是在弘治、正德、嘉靖、万历间。因此,我们无法知道它们最初刊本的“回目”是怎样一个情况。即便是到了明中叶,上述诸小说已有文本留到今天,但其中所体现的“回目”的撰写水平亦极端参差不齐。《三国志通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均是单句回目标题,只是简单的人名、地名、事件的结合,非常实用,但很粗糙。《三遂平妖传》虽是偶句作目,但两句之间多半并不对仗。如第七回“八角井卜吉遇圣姑姑,献金鼎刺配卜吉密州”,第十三回“永儿卖泥烛诱王则,圣姑姑教王则造反”。这样的“回目”,连最起码的偶句对仗的常识都不具备,显得十分幼稚可笑。至于《水浒传》的回目则十分特别,它不仅每回都用偶句作目,而且每条回目都对仗工稳、平仄和谐。如此精美的回目,不要说上述几部作品中没有出现,就是明代中后期的章回小说也未必全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例如肯定产生于《水浒传》之后的万历本《金瓶梅词话》的回目,就如同《三遂平妖传》一样杂乱不堪,甚至连上下两句的字数都参差不齐。如其开卷第一回的回目即为“井阳岗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诚可谓“七上八下”,大不对称。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早期章回小说回目的演变是沿着一条“单句作目”——“不对称的偶句作目”——“精美的对偶句作目”的道路前进的,而只能说明从明初到明中叶,章回小说的回目是优劣有差、高低不等的。这是根据现存文本给我们所提供的证据而后所得出的结论。但有三点必须说明:其一,明中叶以前章回小说的回目已置于每回回首。其二,它的主要功能是叙事,即用最精练的语言概括某回书的故事梗概。其三,它的基本格式是人名、地名、事件的相加。总之,它们显得十分朴素,即便是《水浒传》那样精美的回目,也是朴素的精美。这时的章回小说回目,基本上是一种客观的“叙述”,并未体现作者的主观感情,也较少“描写”的意味。
明末清初,随着章回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它的回目也花样翻新,愈来愈追求形式美,甚至出现“唯美”倾向,走极端者则沦为文字游戏。小说作者们在撰写回目时,除了注意到它的实用性(概括故事内容)而外,还注意到它的艺术性、趣味性,从抒情、状景、诙谐、讽刺、哲理等各个方面加以表现,使读者在未读正文之前,一看回目,就能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这些小说回目已打破了单纯叙事的常规,而具有新鲜趣味。大致而言,有如下几种情况。
其一,抒情。如《春柳莺》第五回回目:“先生羞认梅花扇,翰林泪读杨柳词。”一“羞认”,一“泪读”,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再如《红楼梦》第十九回回目:“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同书第九十八回回目:“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象这样一些回目,不仅能体现书中人物或作者的主观感情,而且还能将这种感情与所叙之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宛如抒情色彩特别浓厚的诗句,能将人带入一种特定的境界。因而,它们本身就是艺术品,是真正意义上的“美文”。
其二,状景。在回目中写景,造成情景交融的妙境,从而为小说内容服务,这也是某些明末清初小说作者的得意之笔。如《人间乐》第八回回目:“云破月来花弄影,春深雷震始知名。”如《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回目:“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膻。”这样一些回目有意识地运用了诸如云、月、花、影、雪、梅等自然界的美景来为书中的人物、故事服务,使人在读小说时似乎看到了一幅又一幅美丽的图画,得到了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
其三,诙谐。通过幽默的语言,造成一种诙谐调侃的效果,明末清初某些小说的作者在这方面具有出奇制胜的本领。如《归莲梦》第五回回目:“无情争似有情痴”,第六回回目:“有情偏被无情恼”。这些从古代诗词中化来的句子,给人一种特别的幽默味儿。再如《麟儿报》第九回回目:“俏媒婆事急充做新人嫁”,以充满生活反常的句子,产生一种调侃揶揄的作用,对书中那位屡屡“试新媒”的媒婆进行了嘲讽。
其四,讽刺。在幽默诙谐的前提下,进一步对社会中的假、丑、恶进行辛辣的嘲讽,在寥寥数字的回目中也能达到这种效果,真让我们对这些作者刮目相看。如《平山冷燕》第五回回目:“山人脸一抹便转”。再如《儒林外史》第三回回目:“胡屠户行凶闹捷报”。前者对那变化无常的“山人”的丑恶嘴脸用最经济的笔墨进行了勾勒,后者却将“行凶”与“报捷”这不可调和的矛盾统一在胡屠户身上,让人看清他那丑得“美妙绝伦”的身段与口吻。
其五,哲理。小小回目,有时甚至能表明生活中所蕴含的某些哲理。从作者那漫不经意的寥寥数语中,读者可以领略到它背后隐藏着的千言万语。《驻春园》第十五回回目曰:“当局意如焚途穷守义,旁观心独醒打点从权。”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一层哲理;途穷守义固然可贵,而从权计议则更是充满无限活力与弹性的人生,是又一层哲理。再如《玉支矶》第九回回目:“无心罗雀罗得了一网全收,有意钓鱼钓不着两头齐跳。”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育柳柳成荫,是一层哲理;用情专一,终有好报,左右徘徊,结局不妙,是又一层哲理。在这里,文字表达、心灵智慧、生活体验,三者融为一体,成为一种警策而美妙的表现。
其六,奇巧。明末清初某些章回小说的作者,作意好奇,卖弄技巧,在回目问题上造成一些饶有趣味的游戏笔墨。如《世无匹》第二回回目:“多情怜白面,干白虹潦倒醉乡;贱价买黄金,金守溪浮沉利海。”既写出了人名、故事,又巧妙地运用了嵌字法。再如《麟儿报》第十四回回目:“你为我走,我因你奔,同行不是伴;他把谁呼,谁将他唤,事急且相随。”虽然长达十余字一句,读起来却琅琅上口。还有《定情人》第八回回目:“痴公子痴的凶,认大姐做小姐;精光棍精得妙,以下人充上人。”既有嵌字,又有反义词的超常组合,真是别有风味。当然,象这样一些回目,弄得过头了,便有文字游戏之嫌,但这卖弄技巧本身,也恰巧说明了作者们对回目的重视,对回目精美的追求。
如果说,明末清初章回小说的回目是在叙事的基础上追求精美的艺术效果的话,那么,清中叶以后的小说回目却向着“精巧”与“实用”两极发展。
一种倾向是对偶句作目,且越拉越长,越来越追求形式美。作者们用尽心机,似乎立志要将回目弄成一种有特殊意味的形式。如《才子奇缘》第二十五回回目:“强谐花烛,水殿元如入笼中之鸟;立时召对,詹兵部难留天上之龙。”又如是书第二十八回回目:“三军奏凯而还,武略与文才兼备;一疏朝天而奏,忠臣与奸党立分。”尽管上下句之间在虚词的运用上有重复之嫌,但每句长达十三字,且颇具韵味。而《自由结婚》一书则有长达十五字一句的标目,如第十五回回目:“一曲浩歌,看步伐止齐,愧杀天下男子;三雄执手,愿隐帆匿楫,避他恶海狂涛。”晚清某些小说的回目,不仅每句长达十余字,甚至能做到音调和谐而又具有诗情画意。如真美善本《孽海花》第三十五回回目:“燕市挥金,豪公子无心结死士;辽天跃马,老英雄仗义送孤臣。”再如《离恨天》第五回回目:“幽室羁囚,一曲悲歌心事写;深宵晤对,两人絮语泪痕多。”此外,这时的小说回目亦有冷嘲热讽的,如《瞎骗奇闻》第五回回目:“山穷水尽,洪士仁犹作补牢心;喝雉呼卢,赵桂森初试牧猪戏。”有的则在讽刺的同时具有文字游戏意味,如《苦社会》第十八回回目:“种痘复种痘,大儿权做小儿;洒水又洒水,恶习斯为美习。”当然,这种将回目文字拉长并加以趣味性的做法,主要是从明末清初小说、尤其是某些才子佳人小说那儿学来的,尚谈不上什么变革,只不过更为极端化而已。
真正使章回小说的回目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的,是清末某些小说中出现的一种由繁而返简,由趣味性而回归实用性的倾向。如《冤狱缘》一书,总共八回,其回目依次如下:“人命之关系,被冤之原因,中毒之奇异,侦探之影响,祖屋之缘由,相片之附卷,破案之离奇,设计之赘婿。”同时,有的作家干脆采取了更简明的两字标目形式,有点象某些明清传奇剧本,也有点象金圣叹评本《西厢记》或张竹坡评本《金瓶梅》的做法。如《宜兴奇案双坛记》《孽报缘》《女学生》《片帆影》《新意外缘》《革命鬼现形记》《秘密自由》《军界风流案》《官场离婚案》等,均乃如此。两字标目,本是一种极简明而又实用的方式,但仍然有略显呆板之不足,于是有的作家则干脆采用更为方便的做法,完全根据情节需要而拟一回目标题,字数多少不限,长短不拘,纯粹单句散文化,最长者可达十几二十字,最短者仅一字,这就使回目的撰写达到了一个极其自由的境地。如三十回本的《新西游记》第四回用一“笑”字标目,第二十二回又以一“偷”字标目,真是省到了极点。此外,诸如《柳非烟》《飞行之怪物》《新痴婆子传》《苏空头》《最近女界秘密史》《吴淑卿义侠传》等作品,全都是单行散文、长短自由的回目标题。更有趣的是,《白云塔》一书,不仅有以一字标目者,如第三:“塔”,第二十三:“火”,而且还有将两个对立的事物放在一个标题里的新奇做法,如第四十:“红;绿”,第四十三:“冷;热”。这的确是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还有《五日缘》一书,回目标题更是与众不同。如第二章:“情丝之交点。”第四章:“托微波以通词。”第十章:“咄!好事之魔。”第十二章:“如斯而已乎?”第十三章:“呜呼大事去。”第十六章:“可怜哉晴天之霹雳。”第十八章:“生离欤?死别欤?”将大量的带有文言虚词的感叹句、疑问句列为标题,又夹以外来词汇,真可谓古今结合、土洋并用,穿西装而戴瓜皮帽,让人如食怪味豆一般,其味也无穷。当然,也有的作品则纯然借用古代诗词曲中的句子、意象,从而将单句散文的回目写得情味盎然。如《鸳鸯碑》共十章,目如次:“我潜身曲槛中”,“好叫我左右做人难”,“猛听得一声去也”,“千种相思向谁说”,“治相思无药饵”,“多管是搁着笔儿未写泪先流”,“有情人成了眷属”,“惨离情半林黄叶”,“这一番花残月缺”,“生则同衾死同穴”。如此回目,真像一篇小小的《西厢》唱辞集锦。总之,章回小说的回目发展到清末,又出现了一个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新局面。
三、小说“回目”的文化意蕴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回目标题大致上经历了一个由粗糙——工整——精致——简约——多元的发展演变过程,而这一过程中所体现的丰富的文化意蕴则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上面我们提到的那些宋元讲史话本多半刊刻于金、元、明时期。对于《新编五代史平话》,“研究者认为本书应是金朝灭亡之前在北方编印的”。(程毅中《新编五代史平话·前言》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话本大系·宣和遗事等两种》)《三国志平话》《乐毅图齐平话》等《全相平话五种》刊刻于元代至治(1321——1323)年间。而《宣和遗事》则为明刻本。从刊刻时间上讲,宋元讲史话本与元杂剧是基本同步的。(元杂剧不可能有金刊本,但元明间刊本颇多)但是,这两种同时生并肩长的兄弟艺术形式的出版效果却大不一样,尤其是将宋元讲史话本的“准回目”与元杂剧的“题目正名”作一比较,就可发现,前者比后者在艺术水平上低一个层次、在发展速度上慢一个节拍。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因为其缔造者的身份、心态不一样之所致。从整体上讲,宋元讲史话本与元杂剧均乃“书会才人”之所为,但元杂剧的作者群中却包含了一些“名公才人”,这些人中,有的就是去职或在职的朝廷官员。正如《录鬼簿》所言:“右前辈公卿,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于乐府留心。”当然,这些“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主要写的是散曲而非杂剧,但即便在元杂剧作家中,也有很多是有“衔头”的。如庾吉甫曾任“中山府判”,马致远曾任“江浙省务官”,李文蔚曾任“瑞昌县尹”,赵天锡曾任“镇江府判”,就连关汉卿,也有人认为他担任过“太医院尹”。而宋元讲史话本的作者,大概永远只能是“无名氏”了。因为话本乃“说话人的底本”,话本的作者实际上就是说话人,如霍四究、尹常卖之类。他们与 “名公”根本沾不上边,只能是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书会才人”,有的甚至只能是“说书艺人”。再者,“说话”在当时只是一种诉诸听觉的艺术形式,根据“说话”整理成的“话本”也并非大量出售给广大读者阅读的,它不象元杂剧的“题目正名”那样是作为一种类似于今天的“海报”的形式贴给观众看的。因此,“准回目”的制作,尚未达到无论是作者、出版者还是读者均追求“美文”的地步。这就是为什么元杂剧的“题目正名”比较工整而宋元讲史话本的“准回目”则显得比较粗糙的根本原因。说到底,二者之间的差别,乃是由它们不同的商业作用、市场需求所决定的。
明代前中期章回小说回目,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小说作者的社会地位、文化修养的不同之所致。这时的章回小说,是从民间长期积累到文人整理加工的转型期。有的小说的回目更多地带有民间通俗文艺的遗留,因此,显得比较粗糙,单句作目,即使是偶句也不对仗。另一方面,有些小说作品因为文人染指其间,不仅偶句作目,甚至对仗工稳,词句妥帖。在这么一个民众创作与文人创作并存的时段,回目状况的杂乱是必然的。但是,有两点却是不能忽视的:其一,将宋元讲史话本正文中的“阴文”标目或书首标目统统置之于每回回首,成为真正的“回目”,这无疑是一大进步。其二,由单句作目变而成为偶句作目,这又是一个更大的进步。更有意义的是,这两大进步又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读者对小说(包括回目)的欣赏水平。人们不仅要读美妙的故事,而且还有看美妙的回目。同样,读者们对回目美文要求的不断提高,又反过来刺激了小说作者注重回目的艺术性。不仅章回小说如此,甚至影响到拟话本小说,冯梦龙编撰“三言”时,一个饶有意味的做法就是:明明是两个不相干的故事,仅仅因为是相邻的两篇,却给它们编了对偶的两句作目,让人读起来琅琅上口。如“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张古老种瓜娶文女,李公子救蛇获称心”等等。而凌�初撰写“二拍”时,则干脆每一个故事都模仿章回小说,来一个偶句作目,且极为工整。这种迎合读者的做法,仍然是一种经济利益驱动的表现。
明末清初章回小说回目愈趋精美,与明中叶的情况不同,它主要不是来自市场经济利益的影响,而是体现了一种文人、尤其是不得志文人一种心灵或才情的寄托。这一类精美的回目多半出现在才子佳人小说或《儒林外史》《红楼梦》这些纯文人创作的小说之中,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天花藏主人在《平山冷燕序》中说得很清楚:“纵福薄时屯,不能羽仪廊庙,为凤为麟,亦可诗酒江湖,为花为柳。”“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曹雪芹也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都将这种心理表现得十分清楚。相比较而言,这些作者对思想寄托、才情展露比经济收入看得更重,甚或有的人根本就没想到经济收入问题。这也是一种文化品格,一种中国传统文人高雅脱俗的文化品格。而晚清某些章回小说回目越写越长、越写越巧的状况,也正是这种文人追求的极端化表现。
至于清末一些章回小说回目由精美到简约并且单句作目的变化,则并非是向着早期章回小说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更高层次的表现。早期章回小说虽多为单句作目,却零散无序,只是一种最低要求,能概括某段故事的大要就行了,并未曾注意到回目自身的艺术性。而清末某些小说的回目,虽不追求“精美”,但却仍然保持着整体的一致性,且同时又体现了一种厌弃繁琐、追求简约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追求,恰恰又是对那种极端表露文人才情而将回目写得“美丽”而“蔓长”的做法的一种反拨,最终形成了五彩缤纷的多元化的回目结构的局面。当然,正如同晚清小说的整体创作状况一样,晚清小说回目的变化也必然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西洋小说的影响。而当我国传统的大众化的通俗文学形式——章回小说最显眼的一笔——回目的构成与西洋小说的形式相结合以后,便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射出新的奇光异彩,同时,也就意味着新的小说标目方式的即将到来。
“回目”的直接来源可追溯到宋元话本。在宋元话本的几大类中,有一类被称之为讲史话本,其基本特点之一是篇幅蔓长,说话艺人在讲这些故事时,并非一、两个单位时间可以讲完,只好逐日分段演讲,这就无形中将这些长篇故事分成了几十乃至几百个段落。为了便于说话艺人讲述和听书人的记忆,也为了使某些精彩的片断更为引人注目,这些话本在出版的时候往往根据故事内容分节立目。这种分节立目的方式,就是回目的雏形。
现存的宋元讲史话本共有十种左右,其分节立目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上图下文,如元刊本《全相平话五种》每一页上栏的图中都有标题,而下栏的文字中亦有以黑地“阴文”标目者,覆盖在相关处的“阳文”之上。例如《全相平话五种》之《三国志平话》中,就有“三战吕布”、“关公刺颜良”、“三谒诸葛”、“赵云抱太子”、“张飞拒水断桥”、“黄忠斩夏侯渊”、“诸葛七擒孟获”、“军师六出歧山”等数十条“阴文”标目,表示精彩的故事段落。《乐毅图齐平话》中亦有“孟子至齐”、“燕国立昭王”等数十条这样的阴文标目。另一种情况是在全书的卷首刊有目录。如士礼居刻本《宣和遗事》书首就有从“历代君王荒淫之失”到“秦桧定都临安”共293条目录。再如董康诵芬室影刻本《景宋残本五代史平话》中除《梁史平话》目录缺佚外,其他四种均书首有目。《唐史平话》有从“论沙陀本末”到“废帝自焚死”计107条目录,《晋史平话》有从“敬瑭割十六州赂契丹”到“契丹主监重贵还本国”计62条目录,《汉史平话》有从“刘知远本沙陀部属”到“推戴郭威为帝”共87条目录,《周史平话》有从“郭威家世业农”到“赵太祖改国号为宋”共94条目录。
一般说来,上述两种情况并不重复出现。也就是说,“阴文”标目者,只随正文标出,在书首却无目录;反之,书首有目录者,正文部分又无“阴文”覆压“阳文”标目。但无论如何,这两种“标目”的情况,正是后世章回小说“回目”之滥觞,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之为“准回目”。
除宋元话本而外,元代杂剧的“题目正名”也给章回小说“回目”的形成以极大的影响。以上所述的阴文标目或书首目录,均为参差不齐的不规则单句作目,只是标明故事大概而已,并非“美文”。而元代杂剧的题目正名却受到骈文和律诗的影响,全是两两相对的偶句,且读起来铿锵作鸣、琅琅上口。如元刊本《看钱奴买冤家债主》题目正名云:“疏财汉典孝子顺孙,看财奴买冤家债主。”再如元刊本《散家财天赐老生儿》题目正名云:“主家妻从夫别父母,卧冰儿祭祖发家私;指绝地死劝糟糠妇,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无论是两句还是四句,都对仗工稳,堪称“美文”。象这样的题目正名,还有元刊本《尉迟恭三夺槊》、《汉高皇濯足气英布》、《风月紫云亭》、《公孙汗衫记》、《薛仁贵衣锦还乡》、《东窗事犯》、《霍光鬼谏》、《严子陵七里滩》、《辅成王周公摄政》、《陈季卿悟道竹叶舟》、《张千替杀妻》等。当然,也有少量对仗不太工稳者,如元刊本《诈妮子调风月》的题目正名:“双莺燕暗争春,诈妮子调风月。”如元刊本《好酒赵元遇上皇》的题目正名:“丈人丈母狠心肠,司公倚势要红妆;雪里公人大报冤,好酒赵元遇上皇。”但无论如何,这些题目正名较之宋元话本的阴文标目或书首目录总要漂亮得多。这些对仗工稳的题目正名,给章回小说的“回目”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二、“回目”的演变
最早的章回小说的回目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实际上是无从说清的。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成书最早的几部章回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等,均无元末或明初的版本。它们的最早出版时间,据目前所知,分别是在弘治、正德、嘉靖、万历间。因此,我们无法知道它们最初刊本的“回目”是怎样一个情况。即便是到了明中叶,上述诸小说已有文本留到今天,但其中所体现的“回目”的撰写水平亦极端参差不齐。《三国志通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均是单句回目标题,只是简单的人名、地名、事件的结合,非常实用,但很粗糙。《三遂平妖传》虽是偶句作目,但两句之间多半并不对仗。如第七回“八角井卜吉遇圣姑姑,献金鼎刺配卜吉密州”,第十三回“永儿卖泥烛诱王则,圣姑姑教王则造反”。这样的“回目”,连最起码的偶句对仗的常识都不具备,显得十分幼稚可笑。至于《水浒传》的回目则十分特别,它不仅每回都用偶句作目,而且每条回目都对仗工稳、平仄和谐。如此精美的回目,不要说上述几部作品中没有出现,就是明代中后期的章回小说也未必全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例如肯定产生于《水浒传》之后的万历本《金瓶梅词话》的回目,就如同《三遂平妖传》一样杂乱不堪,甚至连上下两句的字数都参差不齐。如其开卷第一回的回目即为“井阳岗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诚可谓“七上八下”,大不对称。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早期章回小说回目的演变是沿着一条“单句作目”——“不对称的偶句作目”——“精美的对偶句作目”的道路前进的,而只能说明从明初到明中叶,章回小说的回目是优劣有差、高低不等的。这是根据现存文本给我们所提供的证据而后所得出的结论。但有三点必须说明:其一,明中叶以前章回小说的回目已置于每回回首。其二,它的主要功能是叙事,即用最精练的语言概括某回书的故事梗概。其三,它的基本格式是人名、地名、事件的相加。总之,它们显得十分朴素,即便是《水浒传》那样精美的回目,也是朴素的精美。这时的章回小说回目,基本上是一种客观的“叙述”,并未体现作者的主观感情,也较少“描写”的意味。
明末清初,随着章回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它的回目也花样翻新,愈来愈追求形式美,甚至出现“唯美”倾向,走极端者则沦为文字游戏。小说作者们在撰写回目时,除了注意到它的实用性(概括故事内容)而外,还注意到它的艺术性、趣味性,从抒情、状景、诙谐、讽刺、哲理等各个方面加以表现,使读者在未读正文之前,一看回目,就能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这些小说回目已打破了单纯叙事的常规,而具有新鲜趣味。大致而言,有如下几种情况。
其一,抒情。如《春柳莺》第五回回目:“先生羞认梅花扇,翰林泪读杨柳词。”一“羞认”,一“泪读”,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再如《红楼梦》第十九回回目:“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同书第九十八回回目:“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象这样一些回目,不仅能体现书中人物或作者的主观感情,而且还能将这种感情与所叙之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宛如抒情色彩特别浓厚的诗句,能将人带入一种特定的境界。因而,它们本身就是艺术品,是真正意义上的“美文”。
其二,状景。在回目中写景,造成情景交融的妙境,从而为小说内容服务,这也是某些明末清初小说作者的得意之笔。如《人间乐》第八回回目:“云破月来花弄影,春深雷震始知名。”如《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回目:“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膻。”这样一些回目有意识地运用了诸如云、月、花、影、雪、梅等自然界的美景来为书中的人物、故事服务,使人在读小说时似乎看到了一幅又一幅美丽的图画,得到了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
其三,诙谐。通过幽默的语言,造成一种诙谐调侃的效果,明末清初某些小说的作者在这方面具有出奇制胜的本领。如《归莲梦》第五回回目:“无情争似有情痴”,第六回回目:“有情偏被无情恼”。这些从古代诗词中化来的句子,给人一种特别的幽默味儿。再如《麟儿报》第九回回目:“俏媒婆事急充做新人嫁”,以充满生活反常的句子,产生一种调侃揶揄的作用,对书中那位屡屡“试新媒”的媒婆进行了嘲讽。
其四,讽刺。在幽默诙谐的前提下,进一步对社会中的假、丑、恶进行辛辣的嘲讽,在寥寥数字的回目中也能达到这种效果,真让我们对这些作者刮目相看。如《平山冷燕》第五回回目:“山人脸一抹便转”。再如《儒林外史》第三回回目:“胡屠户行凶闹捷报”。前者对那变化无常的“山人”的丑恶嘴脸用最经济的笔墨进行了勾勒,后者却将“行凶”与“报捷”这不可调和的矛盾统一在胡屠户身上,让人看清他那丑得“美妙绝伦”的身段与口吻。
其五,哲理。小小回目,有时甚至能表明生活中所蕴含的某些哲理。从作者那漫不经意的寥寥数语中,读者可以领略到它背后隐藏着的千言万语。《驻春园》第十五回回目曰:“当局意如焚途穷守义,旁观心独醒打点从权。”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一层哲理;途穷守义固然可贵,而从权计议则更是充满无限活力与弹性的人生,是又一层哲理。再如《玉支矶》第九回回目:“无心罗雀罗得了一网全收,有意钓鱼钓不着两头齐跳。”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育柳柳成荫,是一层哲理;用情专一,终有好报,左右徘徊,结局不妙,是又一层哲理。在这里,文字表达、心灵智慧、生活体验,三者融为一体,成为一种警策而美妙的表现。
其六,奇巧。明末清初某些章回小说的作者,作意好奇,卖弄技巧,在回目问题上造成一些饶有趣味的游戏笔墨。如《世无匹》第二回回目:“多情怜白面,干白虹潦倒醉乡;贱价买黄金,金守溪浮沉利海。”既写出了人名、故事,又巧妙地运用了嵌字法。再如《麟儿报》第十四回回目:“你为我走,我因你奔,同行不是伴;他把谁呼,谁将他唤,事急且相随。”虽然长达十余字一句,读起来却琅琅上口。还有《定情人》第八回回目:“痴公子痴的凶,认大姐做小姐;精光棍精得妙,以下人充上人。”既有嵌字,又有反义词的超常组合,真是别有风味。当然,象这样一些回目,弄得过头了,便有文字游戏之嫌,但这卖弄技巧本身,也恰巧说明了作者们对回目的重视,对回目精美的追求。
如果说,明末清初章回小说的回目是在叙事的基础上追求精美的艺术效果的话,那么,清中叶以后的小说回目却向着“精巧”与“实用”两极发展。
一种倾向是对偶句作目,且越拉越长,越来越追求形式美。作者们用尽心机,似乎立志要将回目弄成一种有特殊意味的形式。如《才子奇缘》第二十五回回目:“强谐花烛,水殿元如入笼中之鸟;立时召对,詹兵部难留天上之龙。”又如是书第二十八回回目:“三军奏凯而还,武略与文才兼备;一疏朝天而奏,忠臣与奸党立分。”尽管上下句之间在虚词的运用上有重复之嫌,但每句长达十三字,且颇具韵味。而《自由结婚》一书则有长达十五字一句的标目,如第十五回回目:“一曲浩歌,看步伐止齐,愧杀天下男子;三雄执手,愿隐帆匿楫,避他恶海狂涛。”晚清某些小说的回目,不仅每句长达十余字,甚至能做到音调和谐而又具有诗情画意。如真美善本《孽海花》第三十五回回目:“燕市挥金,豪公子无心结死士;辽天跃马,老英雄仗义送孤臣。”再如《离恨天》第五回回目:“幽室羁囚,一曲悲歌心事写;深宵晤对,两人絮语泪痕多。”此外,这时的小说回目亦有冷嘲热讽的,如《瞎骗奇闻》第五回回目:“山穷水尽,洪士仁犹作补牢心;喝雉呼卢,赵桂森初试牧猪戏。”有的则在讽刺的同时具有文字游戏意味,如《苦社会》第十八回回目:“种痘复种痘,大儿权做小儿;洒水又洒水,恶习斯为美习。”当然,这种将回目文字拉长并加以趣味性的做法,主要是从明末清初小说、尤其是某些才子佳人小说那儿学来的,尚谈不上什么变革,只不过更为极端化而已。
真正使章回小说的回目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的,是清末某些小说中出现的一种由繁而返简,由趣味性而回归实用性的倾向。如《冤狱缘》一书,总共八回,其回目依次如下:“人命之关系,被冤之原因,中毒之奇异,侦探之影响,祖屋之缘由,相片之附卷,破案之离奇,设计之赘婿。”同时,有的作家干脆采取了更简明的两字标目形式,有点象某些明清传奇剧本,也有点象金圣叹评本《西厢记》或张竹坡评本《金瓶梅》的做法。如《宜兴奇案双坛记》《孽报缘》《女学生》《片帆影》《新意外缘》《革命鬼现形记》《秘密自由》《军界风流案》《官场离婚案》等,均乃如此。两字标目,本是一种极简明而又实用的方式,但仍然有略显呆板之不足,于是有的作家则干脆采用更为方便的做法,完全根据情节需要而拟一回目标题,字数多少不限,长短不拘,纯粹单句散文化,最长者可达十几二十字,最短者仅一字,这就使回目的撰写达到了一个极其自由的境地。如三十回本的《新西游记》第四回用一“笑”字标目,第二十二回又以一“偷”字标目,真是省到了极点。此外,诸如《柳非烟》《飞行之怪物》《新痴婆子传》《苏空头》《最近女界秘密史》《吴淑卿义侠传》等作品,全都是单行散文、长短自由的回目标题。更有趣的是,《白云塔》一书,不仅有以一字标目者,如第三:“塔”,第二十三:“火”,而且还有将两个对立的事物放在一个标题里的新奇做法,如第四十:“红;绿”,第四十三:“冷;热”。这的确是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还有《五日缘》一书,回目标题更是与众不同。如第二章:“情丝之交点。”第四章:“托微波以通词。”第十章:“咄!好事之魔。”第十二章:“如斯而已乎?”第十三章:“呜呼大事去。”第十六章:“可怜哉晴天之霹雳。”第十八章:“生离欤?死别欤?”将大量的带有文言虚词的感叹句、疑问句列为标题,又夹以外来词汇,真可谓古今结合、土洋并用,穿西装而戴瓜皮帽,让人如食怪味豆一般,其味也无穷。当然,也有的作品则纯然借用古代诗词曲中的句子、意象,从而将单句散文的回目写得情味盎然。如《鸳鸯碑》共十章,目如次:“我潜身曲槛中”,“好叫我左右做人难”,“猛听得一声去也”,“千种相思向谁说”,“治相思无药饵”,“多管是搁着笔儿未写泪先流”,“有情人成了眷属”,“惨离情半林黄叶”,“这一番花残月缺”,“生则同衾死同穴”。如此回目,真像一篇小小的《西厢》唱辞集锦。总之,章回小说的回目发展到清末,又出现了一个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新局面。
三、小说“回目”的文化意蕴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回目标题大致上经历了一个由粗糙——工整——精致——简约——多元的发展演变过程,而这一过程中所体现的丰富的文化意蕴则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上面我们提到的那些宋元讲史话本多半刊刻于金、元、明时期。对于《新编五代史平话》,“研究者认为本书应是金朝灭亡之前在北方编印的”。(程毅中《新编五代史平话·前言》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话本大系·宣和遗事等两种》)《三国志平话》《乐毅图齐平话》等《全相平话五种》刊刻于元代至治(1321——1323)年间。而《宣和遗事》则为明刻本。从刊刻时间上讲,宋元讲史话本与元杂剧是基本同步的。(元杂剧不可能有金刊本,但元明间刊本颇多)但是,这两种同时生并肩长的兄弟艺术形式的出版效果却大不一样,尤其是将宋元讲史话本的“准回目”与元杂剧的“题目正名”作一比较,就可发现,前者比后者在艺术水平上低一个层次、在发展速度上慢一个节拍。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因为其缔造者的身份、心态不一样之所致。从整体上讲,宋元讲史话本与元杂剧均乃“书会才人”之所为,但元杂剧的作者群中却包含了一些“名公才人”,这些人中,有的就是去职或在职的朝廷官员。正如《录鬼簿》所言:“右前辈公卿,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于乐府留心。”当然,这些“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主要写的是散曲而非杂剧,但即便在元杂剧作家中,也有很多是有“衔头”的。如庾吉甫曾任“中山府判”,马致远曾任“江浙省务官”,李文蔚曾任“瑞昌县尹”,赵天锡曾任“镇江府判”,就连关汉卿,也有人认为他担任过“太医院尹”。而宋元讲史话本的作者,大概永远只能是“无名氏”了。因为话本乃“说话人的底本”,话本的作者实际上就是说话人,如霍四究、尹常卖之类。他们与 “名公”根本沾不上边,只能是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书会才人”,有的甚至只能是“说书艺人”。再者,“说话”在当时只是一种诉诸听觉的艺术形式,根据“说话”整理成的“话本”也并非大量出售给广大读者阅读的,它不象元杂剧的“题目正名”那样是作为一种类似于今天的“海报”的形式贴给观众看的。因此,“准回目”的制作,尚未达到无论是作者、出版者还是读者均追求“美文”的地步。这就是为什么元杂剧的“题目正名”比较工整而宋元讲史话本的“准回目”则显得比较粗糙的根本原因。说到底,二者之间的差别,乃是由它们不同的商业作用、市场需求所决定的。
明代前中期章回小说回目,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小说作者的社会地位、文化修养的不同之所致。这时的章回小说,是从民间长期积累到文人整理加工的转型期。有的小说的回目更多地带有民间通俗文艺的遗留,因此,显得比较粗糙,单句作目,即使是偶句也不对仗。另一方面,有些小说作品因为文人染指其间,不仅偶句作目,甚至对仗工稳,词句妥帖。在这么一个民众创作与文人创作并存的时段,回目状况的杂乱是必然的。但是,有两点却是不能忽视的:其一,将宋元讲史话本正文中的“阴文”标目或书首标目统统置之于每回回首,成为真正的“回目”,这无疑是一大进步。其二,由单句作目变而成为偶句作目,这又是一个更大的进步。更有意义的是,这两大进步又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读者对小说(包括回目)的欣赏水平。人们不仅要读美妙的故事,而且还有看美妙的回目。同样,读者们对回目美文要求的不断提高,又反过来刺激了小说作者注重回目的艺术性。不仅章回小说如此,甚至影响到拟话本小说,冯梦龙编撰“三言”时,一个饶有意味的做法就是:明明是两个不相干的故事,仅仅因为是相邻的两篇,却给它们编了对偶的两句作目,让人读起来琅琅上口。如“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张古老种瓜娶文女,李公子救蛇获称心”等等。而凌�初撰写“二拍”时,则干脆每一个故事都模仿章回小说,来一个偶句作目,且极为工整。这种迎合读者的做法,仍然是一种经济利益驱动的表现。
明末清初章回小说回目愈趋精美,与明中叶的情况不同,它主要不是来自市场经济利益的影响,而是体现了一种文人、尤其是不得志文人一种心灵或才情的寄托。这一类精美的回目多半出现在才子佳人小说或《儒林外史》《红楼梦》这些纯文人创作的小说之中,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天花藏主人在《平山冷燕序》中说得很清楚:“纵福薄时屯,不能羽仪廊庙,为凤为麟,亦可诗酒江湖,为花为柳。”“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曹雪芹也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都将这种心理表现得十分清楚。相比较而言,这些作者对思想寄托、才情展露比经济收入看得更重,甚或有的人根本就没想到经济收入问题。这也是一种文化品格,一种中国传统文人高雅脱俗的文化品格。而晚清某些章回小说回目越写越长、越写越巧的状况,也正是这种文人追求的极端化表现。
至于清末一些章回小说回目由精美到简约并且单句作目的变化,则并非是向着早期章回小说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更高层次的表现。早期章回小说虽多为单句作目,却零散无序,只是一种最低要求,能概括某段故事的大要就行了,并未曾注意到回目自身的艺术性。而清末某些小说的回目,虽不追求“精美”,但却仍然保持着整体的一致性,且同时又体现了一种厌弃繁琐、追求简约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追求,恰恰又是对那种极端表露文人才情而将回目写得“美丽”而“蔓长”的做法的一种反拨,最终形成了五彩缤纷的多元化的回目结构的局面。当然,正如同晚清小说的整体创作状况一样,晚清小说回目的变化也必然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西洋小说的影响。而当我国传统的大众化的通俗文学形式——章回小说最显眼的一笔——回目的构成与西洋小说的形式相结合以后,便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射出新的奇光异彩,同时,也就意味着新的小说标目方式的即将到来。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9-02-08
就同现在的章节一样。
第2个回答 2009-02-08
标题
可以说是每篇的概括
可以说是每篇的概括
第3个回答 2020-02-21
题目的意思的%:
第4个回答 2018-02-22
一、“回目”之来源
“回目”的直接来源可追溯到宋元话本。在宋元话本的几大类中,有一类被称之为讲史话本,其基本特点之一是篇幅蔓长,说话艺人在讲这些故事时,并非一、两个单位时间可以讲完,只好逐日分段演讲,这就无形中将这些长篇故事分成了几十乃至几百个段落。为了便于说话艺人讲述和听书人的记忆,也为了使某些精彩的片断更为引人注目,这些话本在出版的时候往往根据故事内容分节立目。这种分节立目的方式,就是回目的雏形。
现存的宋元讲史话本共有十种左右,其分节立目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上图下文,如元刊本《全相平话五种》每一页上栏的图中都有标题,而下栏的文字中亦有以黑地“阴文”标目者,覆盖在相关处的“阳文”之上。例如《全相平话五种》之《三国志平话》中,就有“三战吕布”、“关公刺颜良”、“三谒诸葛”、“赵云抱太子”、“张飞拒水断桥”、“黄忠斩夏侯渊”、“诸葛七擒孟获”、“军师六出歧山”等数十条“阴文”标目,表示精彩的故事段落。《乐毅图齐平话》中亦有“孟子至齐”、“燕国立昭王”等数十条这样的阴文标目。另一种情况是在全书的卷首刊有目录。如士礼居刻本《宣和遗事》书首就有从“历代君王荒淫之失”到“秦桧定都临安”共293条目录。再如董康诵芬室影刻本《景宋残本五代史平话》中除《梁史平话》目录缺佚外,其他四种均书首有目。《唐史平话》有从“论沙陀本末”到“废帝自焚死”计107条目录,《晋史平话》有从“敬瑭割十六州赂契丹”到“契丹主监重贵还本国”计62条目录,《汉史平话》有从“刘知远本沙陀部属”到“推戴郭威为帝”共87条目录,《周史平话》有从“郭威家世业农”到“赵太祖改国号为宋”共94条目录。
一般说来,上述两种情况并不重复出现。也就是说,“阴文”标目者,只随正文标出,在书首却无目录;反之,书首有目录者,正文部分又无“阴文”覆压“阳文”标目。但无论如何,这两种“标目”的情况,正是后世章回小说“回目”之滥觞,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之为“准回目”。
除宋元话本而外,元代杂剧的“题目正名”也给章回小说“回目”的形成以极大的影响。以上所述的阴文标目或书首目录,均为参差不齐的不规则单句作目,只是标明故事大概而已,并非“美文”。而元代杂剧的题目正名却受到骈文和律诗的影响,全是两两相对的偶句,且读起来铿锵作鸣、琅琅上口。如元刊本《看钱奴买冤家债主》题目正名云:“疏财汉典孝子顺孙,看财奴买冤家债主。”再如元刊本《散家财天赐老生儿》题目正名云:“主家妻从夫别父母,卧冰儿祭祖发家私;指绝地死劝糟糠妇,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无论是两句还是四句,都对仗工稳,堪称“美文”。象这样的题目正名,还有元刊本《尉迟恭三夺槊》、《汉高皇濯足气英布》、《风月紫云亭》、《公孙汗衫记》、《薛仁贵衣锦还乡》、《东窗事犯》、《霍光鬼谏》、《严子陵七里滩》、《辅成王周公摄政》、《陈季卿悟道竹叶舟》、《张千替杀妻》等。当然,也有少量对仗不太工稳者,如元刊本《诈妮子调风月》的题目正名:“双莺燕暗争春,诈妮子调风月。”如元刊本《好酒赵元遇上皇》的题目正名:“丈人丈母狠心肠,司公倚势要红妆;雪里公人大报冤,好酒赵元遇上皇。”但无论如何,这些题目正名较之宋元话本的阴文标目或书首目录总要漂亮得多。这些对仗工稳的题目正名,给章回小说的“回目”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二、“回目”的演变
最早的章回小说的回目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实际上是无从说清的。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成书最早的几部章回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等,均无元末或明初的版本。它们的最早出版时间,据目前所知,分别是在弘治、正德、嘉靖、万历间。因此,我们无法知道它们最初刊本的“回目”是怎样一个情况。即便是到了明中叶,上述诸小说已有文本留到今天,但其中所体现的“回目”的撰写水平亦极端参差不齐。《三国志通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均是单句回目标题,只是简单的人名、地名、事件的结合,非常实用,但很粗糙。《三遂平妖传》虽是偶句作目,但两句之间多半并不对仗。如第七回“八角井卜吉遇圣姑姑,献金鼎刺配卜吉密州”,第十三回“永儿卖泥烛诱王则,圣姑姑教王则造反”。这样的“回目”,连最起码的偶句对仗的常识都不具备,显得十分幼稚可笑。至于《水浒传》的回目则十分特别,它不仅每回都用偶句作目,而且每条回目都对仗工稳、平仄和谐。如此精美的回目,不要说上述几部作品中没有出现,就是明代中后期的章回小说也未必全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例如肯定产生于《水浒传》之后的万历本《金瓶梅词话》的回目,就如同《三遂平妖传》一样杂乱不堪,甚至连上下两句的字数都参差不齐。如其开卷第一回的回目即为“井阳岗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诚可谓“七上八下”,大不对称。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早期章回小说回目的演变是沿着一条“单句作目”——“不对称的偶句作目”——“精美的对偶句作目”的道路前进的,而只能说明从明初到明中叶,章回小说的回目是优劣有差、高低不等的。这是根据现存文本给我们所提供的证据而后所得出的结论。但有三点必须说明:其一,明中叶以前章回小说的回目已置于每回回首。其二,它的主要功能是叙事,即用最精练的语言概括某回书的故事梗概。其三,它的基本格式是人名、地名、事件的相加。总之,它们显得十分朴素,即便是《水浒传》那样精美的回目,也是朴素的精美。这时的章回小说回目,基本上是一种客观的“叙述”,并未体现作者的主观感情,也较少“描写”的意味。
明末清初,随着章回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它的回目也花样翻新,愈来愈追求形式美,甚至出现“唯美”倾向,走极端者则沦为文字游戏。小说作者们在撰写回目时,除了注意到它的实用性(概括故事内容)而外,还注意到它的艺术性、趣味性,从抒情、状景、诙谐、讽刺、哲理等各个方面加以表现,使读者在未读正文之前,一看回目,就能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这些小说回目已打破了单纯叙事的常规,而具有新鲜趣味。大致而言,有如下几种情况。
其一,抒情。如《春柳莺》第五回回目:“先生羞认梅花扇,翰林泪读杨柳词。”一“羞认”,一“泪读”,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再如《红楼梦》第十九回回目:“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同书第九十八回回目:“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象这样一些回目,不仅能体现书中人物或作者的主观感情,而且还能将这种感情与所叙之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宛如抒情色彩特别浓厚的诗句,能将人带入一种特定的境界。因而,它们本身就是艺术品,是真正意义上的“美文”。
其二,状景。在回目中写景,造成情景交融的妙境,从而为小说内容服务,这也是某些明末清初小说作者的得意之笔。如《人间乐》第八回回目:“云破月来花弄影,春深雷震始知名。”如《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回目:“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膻。”这样一些回目有意识地运用了诸如云、月、花、影、雪、梅等自然界的美景来为书中的人物、故事服务,使人在读小说时似乎看到了一幅又一幅美丽的图画,得到了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
其三,诙谐。通过幽默的语言,造成一种诙谐调侃的效果,明末清初某些小说的作者在这方面具有出奇制胜的本领。如《归莲梦》第五回回目:“无情争似有情痴”,第六回回目:“有情偏被无情恼”。这些从古代诗词中化来的句子,给人一种特别的幽默味儿。再如《麟儿报》第九回回目:“俏媒婆事急充做新人嫁”,以充满生活反常的句子,产生一种调侃揶揄的作用,对书中那位屡屡“试新媒”的媒婆进行了嘲讽。
其四,讽刺。在幽默诙谐的前提下,进一步对社会中的假、丑、恶进行辛辣的嘲讽,在寥寥数字的回目中也能达到这种效果,真让我们对这些作者刮目相看。如《平山冷燕》第五回回目:“山人脸一抹便转”。再如《儒林外史》第三回回目:“胡屠户行凶闹捷报”。前者对那变化无常的“山人”的丑恶嘴脸用最经济的笔墨进行了勾勒,后者却将“行凶”与“报捷”这不可调和的矛盾统一在胡屠户身上,让人看清他那丑得“美妙绝伦”的身段与口吻。
其五,哲理。小小回目,有时甚至能表明生活中所蕴含的某些哲理。从作者那漫不经意的寥寥数语中,读者可以领略到它背后隐藏着的千言万语。《驻春园》第十五回回目曰:“当局意如焚途穷守义,旁观心独醒打点从权。”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一层哲理;途穷守义固然可贵,而从权计议则更是充满无限活力与弹性的人生,是又一层哲理。再如《玉支矶》第九回回目:“无心罗雀罗得了一网全收,有意钓鱼钓不着两头齐跳。”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育柳柳成荫,是一层哲理;用情专一,终有好报,左右徘徊,结局不妙,是又一层哲理。在这里,文字表达、心灵智慧、生活体验,三者融为一体,成为一种警策而美妙的表现。
其六,奇巧。明末清初某些章回小说的作者,作意好奇,卖弄技巧,在回目问题上造成一些饶有趣味的游戏笔墨。如《世无匹》第二回回目:“多情怜白面,干白虹潦倒醉乡;贱价买黄金,金守溪浮沉利海。”既写出了人名、故事,又巧妙地运用了嵌字法。再如《麟儿报》第十四回回目:“你为我走,我因你奔,同行不是伴;他把谁呼,谁将他唤,事急且相随。”虽然长达十余字一句,读起来却琅琅上口。还有《定情人》第八回回目:“痴公子痴的凶,认大姐做小姐;精光棍精得妙,以下人充上人。”既有嵌字,又有反义词的超常组合,真是别有风味。当然,象这样一些回目,弄得过头了,便有文字游戏之嫌,但这卖弄技巧本身,也恰巧说明了作者们对回目的重视,对回目精美的追求。
如果说,明末清初章回小说的回目是在叙事的基础上追求精美的艺术效果的话,那么,清中叶以后的小说回目却向着“精巧”与“实用”两极发展。
一种倾向是对偶句作目,且越拉越长,越来越追求形式美。作者们用尽心机,似乎立志要将回目弄成一种有特殊意味的形式。如《才子奇缘》第二十五回回目:“强谐花烛,水殿元如入笼中之鸟;立时召对,詹兵部难留天上之龙。”又如是书第二十八回回目:“三军奏凯而还,武略与文才兼备;一疏朝天而奏,忠臣与奸党立分。”尽管上下句之间在虚词的运用上有重复之嫌,但每句长达十三字,且颇具韵味。而《自由结婚》一书则有长达十五字一句的标目,如第十五回回目:“一曲浩歌,看步伐止齐,愧杀天下男子;三雄执手,愿隐帆匿楫,避他恶海狂涛。”晚清某些小说的回目,不仅每句长达十余字,甚至能做到音调和谐而又具有诗情画意。如真美善本《孽海花》第三十五回回目:“燕市挥金,豪公子无心结死士;辽天跃马,老英雄仗义送孤臣。”再如《离恨天》第五回回目:“幽室羁囚,一曲悲歌心事写;深宵晤对,两人絮语泪痕多。”此外,这时的小说回目亦有冷嘲热讽的,如《瞎骗奇闻》第五回回目:“山穷水尽,洪士仁犹作补牢心;喝雉呼卢,赵桂森初试牧猪戏。”有的则在讽刺的同时具有文字游戏意味,如《苦社会》第十八回回目:“种痘复种痘,大儿权做小儿;洒水又洒水,恶习斯为美习。”当然,这种将回目文字拉长并加以趣味性的做法,主要是从明末清初小说、尤其是某些才子佳人小说那儿学来的,尚谈不上什么变革,只不过更为极端化而已。
真正使章回小说的回目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的,是清末某些小说中出现的一种由繁而返简,由趣味性而回归实用性的倾向。如《冤狱缘》一书,总共八回,其回目依次如下:“人命之关系,被冤之原因,中毒之奇异,侦探之影响,祖屋之缘由,相片之附卷,破案之离奇,设计之赘婿。”同时,有的作家干脆采取了更简明的两字标目形式,有点象某些明清传奇剧本,也有点象金圣叹评本《西厢记》或张竹坡评本《金瓶梅》的做法。如《宜兴奇案双坛记》《孽报缘》《女学生》《片帆影》《新意外缘》《革命鬼现形记》《秘密自由》《军界风流案》《官场离婚案》等,均乃如此。两字标目,本是一种极简明而又实用的方式,但仍然有略显呆板之不足,于是有的作家则干脆采用更为方便的做法,完全根据情节需要而拟一回目标题,字数多少不限,长短不拘,纯粹单句散文化,最长者可达十几二十字,最短者仅一字,这就使回目的撰写达到了一个极其自由的境地。如三十回本的《新西游记》第四回用一“笑”字标目,第二十二回又以一“偷”字标目,真是省到了极点。此外,诸如《柳非烟》《飞行之怪物》《新痴婆子传》《苏空头》《最近女界秘密史》《吴淑卿义侠传》等作品,全都是单行散文、长短自由的回目标题。更有趣的是,《白云塔》一书,不仅有以一字标目者,如第三:“塔”,第二十三:“火”,而且还有将两个对立的事物放在一个标题里的新奇做法,如第四十:“红;绿”,第四十三:“冷;热”。这的确是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还有《五日缘》一书,回目标题更是与众不同。如第二章:“情丝之交点。”第四章:“托微波以通词。”第十章:“咄!好事之魔。”第十二章:“如斯而已乎?”第十三章:“呜呼大事去。”第十六章:“可怜哉晴天之霹雳。”第十八章:“生离欤?死别欤?”将大量的带有文言虚词的感叹句、疑问句列为标题,又夹以外来词汇,真可谓古今结合、土洋并用,穿西装而戴瓜皮帽,让人如食怪味豆一般,其味也无穷。当然,也有的作品则纯然借用古代诗词曲中的句子、意象,从而将单句散文的回目写得情味盎然。如《鸳鸯碑》共十章,目如次:“我潜身曲槛中”,“好叫我左右做人难”,“猛听得一声去也”,“千种相思向谁说”,“治相思无药饵”,“多管是搁着笔儿未写泪先流”,“有情人成了眷属”,“惨离情半林黄叶”,“这一番花残月缺”,“生则同衾死同穴”。如此回目,真像一篇小小的《西厢》唱辞集锦。总之,章回小说的回目发展到清末,又出现了一个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新局面。
三、小说“回目”的文化意蕴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回目标题大致上经历了一个由粗糙——工整——精致——简约——多元的发展演变过程,而这一过程中所体现的丰富的文化意蕴则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上面我们提到的那些宋元讲史话本多半刊刻于金、元、明时期。对于《新编五代史平话》,“研究者认为本书应是金朝灭亡之前在北方编印的”。(程毅中《新编五代史平话·前言》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话本大系·宣和遗事等两种》)《三国志平话》《乐毅图齐平话》等《全相平话五种》刊刻于元代至治(1321——1323)年间。而《宣和遗事》则为明刻本。从刊刻时间上讲,宋元讲史话本与元杂剧是基本同步的。(元杂剧不可能有金刊本,但元明间刊本颇多)但是,这两种同时生并肩长的兄弟艺术形式的出版效果却大不一样,尤其是将宋元讲史话本的“准回目”与元杂剧的“题目正名”作一比较,就可发现,前者比后者在艺术水平上低一个层次、在发展速度上慢一个节拍。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因为其缔造者的身份、心态不一样之所致。从整体上讲,宋元讲史话本与元杂剧均乃“书会才人”之所为,但元杂剧的作者群中却包含了一些“名公才人”,这些人中,有的就是去职或在职的朝廷官员。正如《录鬼簿》所言:“右前辈公卿,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于乐府留心。”当然,这些“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主要写的是散曲而非杂剧,但即便在元杂剧作家中,也有很多是有“衔头”的。如庾吉甫曾任“中山府判”,马致远曾任“江浙省务官”,李文蔚曾任“瑞昌县尹”,赵天锡曾任“镇江府判”,就连关汉卿,也有人认为他担任过“太医院尹”。而宋元讲史话本的作者,大概永远只能是“无名氏”了。因为话本乃“说话人的底本”,话本的作者实际上就是说话人,如霍四究、尹常卖之类。他们与 “名公”根本沾不上边,只能是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书会才人”,有的甚至只能是“说书艺人”。再者,“说话”在当时只是一种诉诸听觉的艺术形式,根据“说话”整理成的“话本”也并非大量出售给广大读者阅读的,它不象元杂剧的“题目正名”那样是作为一种类似于今天的“海报”的形式贴给观众看的。因此,“准回目”的制作,尚未达到无论是作者、出版者还是读者均追求“美文”的地步。这就是为什么元杂剧的“题目正名”比较工整而宋元讲史话本的“准回目”则显得比较粗糙的根本原因。说到底,二者之间的差别,乃是由它们不同的商业作用、市场需求所决定的。
明代前中期章回小说回目,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小说作者的社会地位、文化修养的不同之所致。这时的章回小说,是从民间长期积累到文人整理加工的转型期。有的小说的回目更多地带有民间通俗文艺的遗留,因此,显得比较粗糙,单句作目,即使是偶句也不对仗。另一方面,有些小说作品因为文人染指其间,不仅偶句作目,甚至对仗工稳,词句妥帖。在这么一个民众创作与文人创作并存的时段,回目状况的杂乱是必然的。但是,有两点却是不能忽视的:其一,将宋元讲史话本正文中的“阴文”标目或书首标目统统置之于每回回首,成为真正的“回目”,这无疑是一大进步。其二,由单句作目变而成为偶句作目,这又是一个更大的进步。更有意义的是,这两大进步又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读者对小说(包括回目)的欣赏水平。人们不仅要读美妙的故事,而且还有看美妙的回目。同样,读者们对回目美文要求的不断提高,又反过来刺激了小说作者注重回目的艺术性。不仅章回小说如此,甚至影响到拟话本小说,冯梦龙编撰“三言”时,一个饶有意味的做法就是:明明是两个不相干的故事,仅仅因为是相邻的两篇,却给它们编了对偶的两句作目,让人读起来琅琅上口。如“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张古老种瓜娶文女,李公子救蛇获称心”等等。而凌?初撰写“二拍”时,则干脆每一个故事都模仿章回小说,来一个偶句作目,且极为工整。这种迎合读者的做法,仍然是一种经济利益驱动的表现。
明末清初章回小说回目愈趋精美,与明中叶的情况不同,它主要不是来自市场经济利益的影响,而是体现了一种文人、尤其是不得志文人一种心灵或才情的寄托。这一类精美的回目多半出现在才子佳人小说或《儒林外史》《红楼梦》这些纯文人创作的小说之中,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天花藏主人在《平山冷燕序》中说得很清楚:“纵福薄时屯,不能羽仪廊庙,为凤为麟,亦可诗酒江湖,为花为柳。”“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曹雪芹也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都将这种心理表现得十分清楚。相比较而言,这些作者对思想寄托、才情展露比经济收入看得更重,甚或有的人根本就没想到经济收入问题。这也是一种文化品格,一种中国传统文人高雅脱俗的文化品格。而晚清某些章回小说回目越写越长、越写越巧的状况,也正是这种文人追求的极端化表现。
至于清末一些章回小说回目由精美到简约并且单句作目的变化,则并非是向着早期章回小说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更高层次的表现。早期章回小说虽多为单句作目,却零散无序,只是一种最低要求,能概括某段故事的大要就行了,并未曾注意到回目自身的艺术性。而清末某些小说的回目,虽不追求“精美”,但却仍然保持着整体的一致性,且同时又体现了一种厌弃繁琐、追求简约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追求,恰恰又是对那种极端表露文人才情而将回目写得“美丽”而“蔓长”的做法的一种反拨,最终形成了五彩缤纷的多元化的回目结构的局面。当然,正如同晚清小说的整体创作状况一样,晚清小说回目的变化也必然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西洋小说的影响。而当我国传统的大众化的通俗文学形式——章回小说最显眼的一笔——回目的构成与西洋小说的形式相结合以后,便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射出新的奇光异彩,同时,也就意味着新的小说标目方式的即将到来。
“回目”的直接来源可追溯到宋元话本。在宋元话本的几大类中,有一类被称之为讲史话本,其基本特点之一是篇幅蔓长,说话艺人在讲这些故事时,并非一、两个单位时间可以讲完,只好逐日分段演讲,这就无形中将这些长篇故事分成了几十乃至几百个段落。为了便于说话艺人讲述和听书人的记忆,也为了使某些精彩的片断更为引人注目,这些话本在出版的时候往往根据故事内容分节立目。这种分节立目的方式,就是回目的雏形。
现存的宋元讲史话本共有十种左右,其分节立目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上图下文,如元刊本《全相平话五种》每一页上栏的图中都有标题,而下栏的文字中亦有以黑地“阴文”标目者,覆盖在相关处的“阳文”之上。例如《全相平话五种》之《三国志平话》中,就有“三战吕布”、“关公刺颜良”、“三谒诸葛”、“赵云抱太子”、“张飞拒水断桥”、“黄忠斩夏侯渊”、“诸葛七擒孟获”、“军师六出歧山”等数十条“阴文”标目,表示精彩的故事段落。《乐毅图齐平话》中亦有“孟子至齐”、“燕国立昭王”等数十条这样的阴文标目。另一种情况是在全书的卷首刊有目录。如士礼居刻本《宣和遗事》书首就有从“历代君王荒淫之失”到“秦桧定都临安”共293条目录。再如董康诵芬室影刻本《景宋残本五代史平话》中除《梁史平话》目录缺佚外,其他四种均书首有目。《唐史平话》有从“论沙陀本末”到“废帝自焚死”计107条目录,《晋史平话》有从“敬瑭割十六州赂契丹”到“契丹主监重贵还本国”计62条目录,《汉史平话》有从“刘知远本沙陀部属”到“推戴郭威为帝”共87条目录,《周史平话》有从“郭威家世业农”到“赵太祖改国号为宋”共94条目录。
一般说来,上述两种情况并不重复出现。也就是说,“阴文”标目者,只随正文标出,在书首却无目录;反之,书首有目录者,正文部分又无“阴文”覆压“阳文”标目。但无论如何,这两种“标目”的情况,正是后世章回小说“回目”之滥觞,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之为“准回目”。
除宋元话本而外,元代杂剧的“题目正名”也给章回小说“回目”的形成以极大的影响。以上所述的阴文标目或书首目录,均为参差不齐的不规则单句作目,只是标明故事大概而已,并非“美文”。而元代杂剧的题目正名却受到骈文和律诗的影响,全是两两相对的偶句,且读起来铿锵作鸣、琅琅上口。如元刊本《看钱奴买冤家债主》题目正名云:“疏财汉典孝子顺孙,看财奴买冤家债主。”再如元刊本《散家财天赐老生儿》题目正名云:“主家妻从夫别父母,卧冰儿祭祖发家私;指绝地死劝糟糠妇,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无论是两句还是四句,都对仗工稳,堪称“美文”。象这样的题目正名,还有元刊本《尉迟恭三夺槊》、《汉高皇濯足气英布》、《风月紫云亭》、《公孙汗衫记》、《薛仁贵衣锦还乡》、《东窗事犯》、《霍光鬼谏》、《严子陵七里滩》、《辅成王周公摄政》、《陈季卿悟道竹叶舟》、《张千替杀妻》等。当然,也有少量对仗不太工稳者,如元刊本《诈妮子调风月》的题目正名:“双莺燕暗争春,诈妮子调风月。”如元刊本《好酒赵元遇上皇》的题目正名:“丈人丈母狠心肠,司公倚势要红妆;雪里公人大报冤,好酒赵元遇上皇。”但无论如何,这些题目正名较之宋元话本的阴文标目或书首目录总要漂亮得多。这些对仗工稳的题目正名,给章回小说的“回目”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二、“回目”的演变
最早的章回小说的回目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实际上是无从说清的。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成书最早的几部章回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等,均无元末或明初的版本。它们的最早出版时间,据目前所知,分别是在弘治、正德、嘉靖、万历间。因此,我们无法知道它们最初刊本的“回目”是怎样一个情况。即便是到了明中叶,上述诸小说已有文本留到今天,但其中所体现的“回目”的撰写水平亦极端参差不齐。《三国志通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均是单句回目标题,只是简单的人名、地名、事件的结合,非常实用,但很粗糙。《三遂平妖传》虽是偶句作目,但两句之间多半并不对仗。如第七回“八角井卜吉遇圣姑姑,献金鼎刺配卜吉密州”,第十三回“永儿卖泥烛诱王则,圣姑姑教王则造反”。这样的“回目”,连最起码的偶句对仗的常识都不具备,显得十分幼稚可笑。至于《水浒传》的回目则十分特别,它不仅每回都用偶句作目,而且每条回目都对仗工稳、平仄和谐。如此精美的回目,不要说上述几部作品中没有出现,就是明代中后期的章回小说也未必全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例如肯定产生于《水浒传》之后的万历本《金瓶梅词话》的回目,就如同《三遂平妖传》一样杂乱不堪,甚至连上下两句的字数都参差不齐。如其开卷第一回的回目即为“井阳岗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诚可谓“七上八下”,大不对称。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早期章回小说回目的演变是沿着一条“单句作目”——“不对称的偶句作目”——“精美的对偶句作目”的道路前进的,而只能说明从明初到明中叶,章回小说的回目是优劣有差、高低不等的。这是根据现存文本给我们所提供的证据而后所得出的结论。但有三点必须说明:其一,明中叶以前章回小说的回目已置于每回回首。其二,它的主要功能是叙事,即用最精练的语言概括某回书的故事梗概。其三,它的基本格式是人名、地名、事件的相加。总之,它们显得十分朴素,即便是《水浒传》那样精美的回目,也是朴素的精美。这时的章回小说回目,基本上是一种客观的“叙述”,并未体现作者的主观感情,也较少“描写”的意味。
明末清初,随着章回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它的回目也花样翻新,愈来愈追求形式美,甚至出现“唯美”倾向,走极端者则沦为文字游戏。小说作者们在撰写回目时,除了注意到它的实用性(概括故事内容)而外,还注意到它的艺术性、趣味性,从抒情、状景、诙谐、讽刺、哲理等各个方面加以表现,使读者在未读正文之前,一看回目,就能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这些小说回目已打破了单纯叙事的常规,而具有新鲜趣味。大致而言,有如下几种情况。
其一,抒情。如《春柳莺》第五回回目:“先生羞认梅花扇,翰林泪读杨柳词。”一“羞认”,一“泪读”,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再如《红楼梦》第十九回回目:“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同书第九十八回回目:“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象这样一些回目,不仅能体现书中人物或作者的主观感情,而且还能将这种感情与所叙之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宛如抒情色彩特别浓厚的诗句,能将人带入一种特定的境界。因而,它们本身就是艺术品,是真正意义上的“美文”。
其二,状景。在回目中写景,造成情景交融的妙境,从而为小说内容服务,这也是某些明末清初小说作者的得意之笔。如《人间乐》第八回回目:“云破月来花弄影,春深雷震始知名。”如《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回目:“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膻。”这样一些回目有意识地运用了诸如云、月、花、影、雪、梅等自然界的美景来为书中的人物、故事服务,使人在读小说时似乎看到了一幅又一幅美丽的图画,得到了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
其三,诙谐。通过幽默的语言,造成一种诙谐调侃的效果,明末清初某些小说的作者在这方面具有出奇制胜的本领。如《归莲梦》第五回回目:“无情争似有情痴”,第六回回目:“有情偏被无情恼”。这些从古代诗词中化来的句子,给人一种特别的幽默味儿。再如《麟儿报》第九回回目:“俏媒婆事急充做新人嫁”,以充满生活反常的句子,产生一种调侃揶揄的作用,对书中那位屡屡“试新媒”的媒婆进行了嘲讽。
其四,讽刺。在幽默诙谐的前提下,进一步对社会中的假、丑、恶进行辛辣的嘲讽,在寥寥数字的回目中也能达到这种效果,真让我们对这些作者刮目相看。如《平山冷燕》第五回回目:“山人脸一抹便转”。再如《儒林外史》第三回回目:“胡屠户行凶闹捷报”。前者对那变化无常的“山人”的丑恶嘴脸用最经济的笔墨进行了勾勒,后者却将“行凶”与“报捷”这不可调和的矛盾统一在胡屠户身上,让人看清他那丑得“美妙绝伦”的身段与口吻。
其五,哲理。小小回目,有时甚至能表明生活中所蕴含的某些哲理。从作者那漫不经意的寥寥数语中,读者可以领略到它背后隐藏着的千言万语。《驻春园》第十五回回目曰:“当局意如焚途穷守义,旁观心独醒打点从权。”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一层哲理;途穷守义固然可贵,而从权计议则更是充满无限活力与弹性的人生,是又一层哲理。再如《玉支矶》第九回回目:“无心罗雀罗得了一网全收,有意钓鱼钓不着两头齐跳。”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育柳柳成荫,是一层哲理;用情专一,终有好报,左右徘徊,结局不妙,是又一层哲理。在这里,文字表达、心灵智慧、生活体验,三者融为一体,成为一种警策而美妙的表现。
其六,奇巧。明末清初某些章回小说的作者,作意好奇,卖弄技巧,在回目问题上造成一些饶有趣味的游戏笔墨。如《世无匹》第二回回目:“多情怜白面,干白虹潦倒醉乡;贱价买黄金,金守溪浮沉利海。”既写出了人名、故事,又巧妙地运用了嵌字法。再如《麟儿报》第十四回回目:“你为我走,我因你奔,同行不是伴;他把谁呼,谁将他唤,事急且相随。”虽然长达十余字一句,读起来却琅琅上口。还有《定情人》第八回回目:“痴公子痴的凶,认大姐做小姐;精光棍精得妙,以下人充上人。”既有嵌字,又有反义词的超常组合,真是别有风味。当然,象这样一些回目,弄得过头了,便有文字游戏之嫌,但这卖弄技巧本身,也恰巧说明了作者们对回目的重视,对回目精美的追求。
如果说,明末清初章回小说的回目是在叙事的基础上追求精美的艺术效果的话,那么,清中叶以后的小说回目却向着“精巧”与“实用”两极发展。
一种倾向是对偶句作目,且越拉越长,越来越追求形式美。作者们用尽心机,似乎立志要将回目弄成一种有特殊意味的形式。如《才子奇缘》第二十五回回目:“强谐花烛,水殿元如入笼中之鸟;立时召对,詹兵部难留天上之龙。”又如是书第二十八回回目:“三军奏凯而还,武略与文才兼备;一疏朝天而奏,忠臣与奸党立分。”尽管上下句之间在虚词的运用上有重复之嫌,但每句长达十三字,且颇具韵味。而《自由结婚》一书则有长达十五字一句的标目,如第十五回回目:“一曲浩歌,看步伐止齐,愧杀天下男子;三雄执手,愿隐帆匿楫,避他恶海狂涛。”晚清某些小说的回目,不仅每句长达十余字,甚至能做到音调和谐而又具有诗情画意。如真美善本《孽海花》第三十五回回目:“燕市挥金,豪公子无心结死士;辽天跃马,老英雄仗义送孤臣。”再如《离恨天》第五回回目:“幽室羁囚,一曲悲歌心事写;深宵晤对,两人絮语泪痕多。”此外,这时的小说回目亦有冷嘲热讽的,如《瞎骗奇闻》第五回回目:“山穷水尽,洪士仁犹作补牢心;喝雉呼卢,赵桂森初试牧猪戏。”有的则在讽刺的同时具有文字游戏意味,如《苦社会》第十八回回目:“种痘复种痘,大儿权做小儿;洒水又洒水,恶习斯为美习。”当然,这种将回目文字拉长并加以趣味性的做法,主要是从明末清初小说、尤其是某些才子佳人小说那儿学来的,尚谈不上什么变革,只不过更为极端化而已。
真正使章回小说的回目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的,是清末某些小说中出现的一种由繁而返简,由趣味性而回归实用性的倾向。如《冤狱缘》一书,总共八回,其回目依次如下:“人命之关系,被冤之原因,中毒之奇异,侦探之影响,祖屋之缘由,相片之附卷,破案之离奇,设计之赘婿。”同时,有的作家干脆采取了更简明的两字标目形式,有点象某些明清传奇剧本,也有点象金圣叹评本《西厢记》或张竹坡评本《金瓶梅》的做法。如《宜兴奇案双坛记》《孽报缘》《女学生》《片帆影》《新意外缘》《革命鬼现形记》《秘密自由》《军界风流案》《官场离婚案》等,均乃如此。两字标目,本是一种极简明而又实用的方式,但仍然有略显呆板之不足,于是有的作家则干脆采用更为方便的做法,完全根据情节需要而拟一回目标题,字数多少不限,长短不拘,纯粹单句散文化,最长者可达十几二十字,最短者仅一字,这就使回目的撰写达到了一个极其自由的境地。如三十回本的《新西游记》第四回用一“笑”字标目,第二十二回又以一“偷”字标目,真是省到了极点。此外,诸如《柳非烟》《飞行之怪物》《新痴婆子传》《苏空头》《最近女界秘密史》《吴淑卿义侠传》等作品,全都是单行散文、长短自由的回目标题。更有趣的是,《白云塔》一书,不仅有以一字标目者,如第三:“塔”,第二十三:“火”,而且还有将两个对立的事物放在一个标题里的新奇做法,如第四十:“红;绿”,第四十三:“冷;热”。这的确是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还有《五日缘》一书,回目标题更是与众不同。如第二章:“情丝之交点。”第四章:“托微波以通词。”第十章:“咄!好事之魔。”第十二章:“如斯而已乎?”第十三章:“呜呼大事去。”第十六章:“可怜哉晴天之霹雳。”第十八章:“生离欤?死别欤?”将大量的带有文言虚词的感叹句、疑问句列为标题,又夹以外来词汇,真可谓古今结合、土洋并用,穿西装而戴瓜皮帽,让人如食怪味豆一般,其味也无穷。当然,也有的作品则纯然借用古代诗词曲中的句子、意象,从而将单句散文的回目写得情味盎然。如《鸳鸯碑》共十章,目如次:“我潜身曲槛中”,“好叫我左右做人难”,“猛听得一声去也”,“千种相思向谁说”,“治相思无药饵”,“多管是搁着笔儿未写泪先流”,“有情人成了眷属”,“惨离情半林黄叶”,“这一番花残月缺”,“生则同衾死同穴”。如此回目,真像一篇小小的《西厢》唱辞集锦。总之,章回小说的回目发展到清末,又出现了一个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新局面。
三、小说“回目”的文化意蕴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回目标题大致上经历了一个由粗糙——工整——精致——简约——多元的发展演变过程,而这一过程中所体现的丰富的文化意蕴则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上面我们提到的那些宋元讲史话本多半刊刻于金、元、明时期。对于《新编五代史平话》,“研究者认为本书应是金朝灭亡之前在北方编印的”。(程毅中《新编五代史平话·前言》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话本大系·宣和遗事等两种》)《三国志平话》《乐毅图齐平话》等《全相平话五种》刊刻于元代至治(1321——1323)年间。而《宣和遗事》则为明刻本。从刊刻时间上讲,宋元讲史话本与元杂剧是基本同步的。(元杂剧不可能有金刊本,但元明间刊本颇多)但是,这两种同时生并肩长的兄弟艺术形式的出版效果却大不一样,尤其是将宋元讲史话本的“准回目”与元杂剧的“题目正名”作一比较,就可发现,前者比后者在艺术水平上低一个层次、在发展速度上慢一个节拍。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因为其缔造者的身份、心态不一样之所致。从整体上讲,宋元讲史话本与元杂剧均乃“书会才人”之所为,但元杂剧的作者群中却包含了一些“名公才人”,这些人中,有的就是去职或在职的朝廷官员。正如《录鬼簿》所言:“右前辈公卿,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于乐府留心。”当然,这些“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主要写的是散曲而非杂剧,但即便在元杂剧作家中,也有很多是有“衔头”的。如庾吉甫曾任“中山府判”,马致远曾任“江浙省务官”,李文蔚曾任“瑞昌县尹”,赵天锡曾任“镇江府判”,就连关汉卿,也有人认为他担任过“太医院尹”。而宋元讲史话本的作者,大概永远只能是“无名氏”了。因为话本乃“说话人的底本”,话本的作者实际上就是说话人,如霍四究、尹常卖之类。他们与 “名公”根本沾不上边,只能是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书会才人”,有的甚至只能是“说书艺人”。再者,“说话”在当时只是一种诉诸听觉的艺术形式,根据“说话”整理成的“话本”也并非大量出售给广大读者阅读的,它不象元杂剧的“题目正名”那样是作为一种类似于今天的“海报”的形式贴给观众看的。因此,“准回目”的制作,尚未达到无论是作者、出版者还是读者均追求“美文”的地步。这就是为什么元杂剧的“题目正名”比较工整而宋元讲史话本的“准回目”则显得比较粗糙的根本原因。说到底,二者之间的差别,乃是由它们不同的商业作用、市场需求所决定的。
明代前中期章回小说回目,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小说作者的社会地位、文化修养的不同之所致。这时的章回小说,是从民间长期积累到文人整理加工的转型期。有的小说的回目更多地带有民间通俗文艺的遗留,因此,显得比较粗糙,单句作目,即使是偶句也不对仗。另一方面,有些小说作品因为文人染指其间,不仅偶句作目,甚至对仗工稳,词句妥帖。在这么一个民众创作与文人创作并存的时段,回目状况的杂乱是必然的。但是,有两点却是不能忽视的:其一,将宋元讲史话本正文中的“阴文”标目或书首标目统统置之于每回回首,成为真正的“回目”,这无疑是一大进步。其二,由单句作目变而成为偶句作目,这又是一个更大的进步。更有意义的是,这两大进步又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读者对小说(包括回目)的欣赏水平。人们不仅要读美妙的故事,而且还有看美妙的回目。同样,读者们对回目美文要求的不断提高,又反过来刺激了小说作者注重回目的艺术性。不仅章回小说如此,甚至影响到拟话本小说,冯梦龙编撰“三言”时,一个饶有意味的做法就是:明明是两个不相干的故事,仅仅因为是相邻的两篇,却给它们编了对偶的两句作目,让人读起来琅琅上口。如“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张古老种瓜娶文女,李公子救蛇获称心”等等。而凌?初撰写“二拍”时,则干脆每一个故事都模仿章回小说,来一个偶句作目,且极为工整。这种迎合读者的做法,仍然是一种经济利益驱动的表现。
明末清初章回小说回目愈趋精美,与明中叶的情况不同,它主要不是来自市场经济利益的影响,而是体现了一种文人、尤其是不得志文人一种心灵或才情的寄托。这一类精美的回目多半出现在才子佳人小说或《儒林外史》《红楼梦》这些纯文人创作的小说之中,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天花藏主人在《平山冷燕序》中说得很清楚:“纵福薄时屯,不能羽仪廊庙,为凤为麟,亦可诗酒江湖,为花为柳。”“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曹雪芹也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都将这种心理表现得十分清楚。相比较而言,这些作者对思想寄托、才情展露比经济收入看得更重,甚或有的人根本就没想到经济收入问题。这也是一种文化品格,一种中国传统文人高雅脱俗的文化品格。而晚清某些章回小说回目越写越长、越写越巧的状况,也正是这种文人追求的极端化表现。
至于清末一些章回小说回目由精美到简约并且单句作目的变化,则并非是向着早期章回小说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更高层次的表现。早期章回小说虽多为单句作目,却零散无序,只是一种最低要求,能概括某段故事的大要就行了,并未曾注意到回目自身的艺术性。而清末某些小说的回目,虽不追求“精美”,但却仍然保持着整体的一致性,且同时又体现了一种厌弃繁琐、追求简约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追求,恰恰又是对那种极端表露文人才情而将回目写得“美丽”而“蔓长”的做法的一种反拨,最终形成了五彩缤纷的多元化的回目结构的局面。当然,正如同晚清小说的整体创作状况一样,晚清小说回目的变化也必然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西洋小说的影响。而当我国传统的大众化的通俗文学形式——章回小说最显眼的一笔——回目的构成与西洋小说的形式相结合以后,便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射出新的奇光异彩,同时,也就意味着新的小说标目方式的即将到来。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