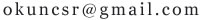少年闰土
----鲁迅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摸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跨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
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弶捉小鸟雀的。
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地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
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
闰土又对我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四瓜去,你也去。”
“管贼吗?”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地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
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刺猬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不知道——只是无端地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
“它不咬人吗?”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它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它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我们沙地里,潮流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
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鲁迅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摸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跨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
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弶捉小鸟雀的。
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地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
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
闰土又对我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四瓜去,你也去。”
“管贼吗?”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地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
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刺猬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不知道——只是无端地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
“它不咬人吗?”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它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它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我们沙地里,潮流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
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9-05-18
转眼,已过而立之年,站在三尺讲台上,书写着学生的未来,展望着祖国的花朵。看着台下一双双天真无邪的眼睛,记忆如水,漫过我童年的原野。
童年,最喜欢邀友结伴,下河捕鱼。家乡有条小河,河水清澈见底,游鱼成群戏于石间。我们或拿箕畚,下河一赶,鱼儿便争先恐后地往水草里钻,只要拿箕畚一挡,脚儿一踩,昏浊的河水中鱼儿辨不清方向,东窜西逃入箕畚,迅速往水面一提,总能看到七八条鱼儿在活蹦乱跳。或挖些蚯蚓,拿条钓杆,在金黄的午后,坐在村后的石桥上钓鱼。蚯蚓是鱼儿的最爱,而乡间的鱼儿大多呆板,不清楚人世间的尔虞我诈,将钓钩往水里一甩,鱼儿就赶趟儿似的上钩。坐上一个下午,也能收获不少。回家交给母亲,又是一道难得的美味佳肴。
捕蜻蜓,也是童年一件少有的趣事。拿根竹杆,顶头系个蔑圈,网就成了。有了网,然后对各个角落大肆搜捕一番,粘上蜘蛛网,要粘粘的那种。乡间五谷杂粮众多,每当花儿飘香时,蜻蜓云集众多,小路上,田埂边,都可看到满是晴蜓的影子,红的,黑的,大的,小的,各式各样都有。我们会蹑手蹑脚地走到蜻蜓身后,竹杆网轻轻下落,蜻蜓就成了瓮中之鳖。而我们也不贪心,往往捕到五六只时,就心满意足而归。再用根细线系在蜻蜓尾部,将它放飞在天宇,如同风筝,起起落落间,承载了童年的欢乐。
童年时,还喜欢上山挖笋,春冬两季均可。扛上一把锄头,带上一个笋兜,在清幽的鸟鸣中,踏入竹林,开始与笋儿的游戏。春笋易寻,它们总爱偷偷钻出地面,露出毛茸茸的小脑袋,落入我们眼帘。冬笋难挖,它们似羞答答的小姑娘,躲在泥土里,就不爱抛头露面。当然,我们乡间的小孩,也多有一套挖笋的本领,朝着西南方向,顺着竹鞭,瞅着有些拱起的地面,一挖一个准。在霞光映红天空时,踩着夕阳而归,笋兜里都能满载而归,回家后,去皮,洗净,切片,放入腌菜,慢火细煮,要不了多久,清香便缭绕满整间屋子。顺着清香,嚼着冬笋,口舌皆酥,多少滋润了穷苦少吃的童年。
如今,时光不再,童年不再,鱼儿不再,蜻蜓不再,笋儿不再,童趣也荡然无存,只能把这些过往的记忆,珍藏在柔软的心底,偶尔品味,也能快乐如斯。
“如果我告诉你们,我很会爬树,你们相信吗?”
是个美丽的星期天,三位因音乐而结缘的朋友,约了共享一顿美食。其实美食是个借口,特别对我这已频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之列的人,但难得的相聚,且任情任性地敞开心怀,天南地北地聊个痛快吧!
话题从最近几场演唱会扯开,不知怎么忽然跳到童年时光。那么遥远遥远的场景,贞和梅兴奋万分地谈她们共同的家乡——马来西亚。两人是透过我而认识的。一直认为对方是台湾人,而且是我这类台湾的外省人。直到这刻。
顷刻间,浓浓的乡情把她们两人的兴致抬得好高,让我这介绍人也感染了喜气。静静地聆听她们的童年往事。长得白皙秀美的贞,儿时却是个常和男生争吵打架的Tom Boy:“个子高,每天在外面玩球,晒得又黑又粗……完全不像个女孩子。”是八年的英国留学生活,将这成长于马来西亚小镇的纯朴姑娘,培育成了典型的城市淑女。
同样高挑秀雅的梅,举手投足比贞更多几分帅气,是近年不时谈心谈艺的好友。与她在音乐欣赏的品味上,常有不期而遇的共鸣,为之惊喜不已。她当年中学毕业,自马来西亚赴台湾读大学,受教于K。三十多年前我们迁居新加坡不久,就与梅照过面。或许因我这“师母”的身份,是层难以穿越的墙吧,尽管早已相识,却要等到多年后,才因音乐剧《歌中情》而成知音。真合了那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梅兴味淋漓地描绘,儿时在马来西亚东海岸乡间的趣事,爬树,捉鱼,偷摘树上水果,被主人追骂等等。骤然间,我的童年也如梦如幻地回到脑际,忍不住打断她说:“如果我告诉你们,我很会爬树,你们相信吗?”“不相信”,两人异口同声。
在树梢头筑梦,游荡的日子,是生命中最初始的快乐源头。从南京来到台湾,战争和逃难的梦魇远去,家已安安稳稳地坐落在台中大肚乡福利新村。一片绿树覆盖满村,而那枝桠相缠的行道树,更让七岁的我练就一身轻功。每天从自家门前出来,先把鞋子脱了,放进书包,爬上第一株树,然后顺着交缠的一枝一桠往前攀爬,直到校门口那株老榕树。轻轻跳下来,把鞋子穿好,书包背妥,乖乖地做那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有两次未及下树,就被校长发现,厉声斥骂:“是哪位同学在树上?赶快下来,再不下来,上去捉你。”尽管心惊胆跳,却硬是屏住气息隐入绿叶丛中,躲过去了。
爬树是每个乡下孩子玩不厌的游戏,也是我这辈子惟一及格的运动。许多许多年后,曾在接受电台访问时,脱口而出:我希望自己是一棵树。因为树上的世界是想象的梦土,是无病无忧的乐园,让童稚的心灵在摇晃的绿影中,忘却家中缠绵病榻的父亲和妹妹。
“一直到今天,一看着树,我就不自觉想,该怎么一步步攀爬上去。”
“那么,你现在还会爬树吗?”
还爬得上树吗?望着窗外浓郁树影,我问自己。(
童年,最喜欢邀友结伴,下河捕鱼。家乡有条小河,河水清澈见底,游鱼成群戏于石间。我们或拿箕畚,下河一赶,鱼儿便争先恐后地往水草里钻,只要拿箕畚一挡,脚儿一踩,昏浊的河水中鱼儿辨不清方向,东窜西逃入箕畚,迅速往水面一提,总能看到七八条鱼儿在活蹦乱跳。或挖些蚯蚓,拿条钓杆,在金黄的午后,坐在村后的石桥上钓鱼。蚯蚓是鱼儿的最爱,而乡间的鱼儿大多呆板,不清楚人世间的尔虞我诈,将钓钩往水里一甩,鱼儿就赶趟儿似的上钩。坐上一个下午,也能收获不少。回家交给母亲,又是一道难得的美味佳肴。
捕蜻蜓,也是童年一件少有的趣事。拿根竹杆,顶头系个蔑圈,网就成了。有了网,然后对各个角落大肆搜捕一番,粘上蜘蛛网,要粘粘的那种。乡间五谷杂粮众多,每当花儿飘香时,蜻蜓云集众多,小路上,田埂边,都可看到满是晴蜓的影子,红的,黑的,大的,小的,各式各样都有。我们会蹑手蹑脚地走到蜻蜓身后,竹杆网轻轻下落,蜻蜓就成了瓮中之鳖。而我们也不贪心,往往捕到五六只时,就心满意足而归。再用根细线系在蜻蜓尾部,将它放飞在天宇,如同风筝,起起落落间,承载了童年的欢乐。
童年时,还喜欢上山挖笋,春冬两季均可。扛上一把锄头,带上一个笋兜,在清幽的鸟鸣中,踏入竹林,开始与笋儿的游戏。春笋易寻,它们总爱偷偷钻出地面,露出毛茸茸的小脑袋,落入我们眼帘。冬笋难挖,它们似羞答答的小姑娘,躲在泥土里,就不爱抛头露面。当然,我们乡间的小孩,也多有一套挖笋的本领,朝着西南方向,顺着竹鞭,瞅着有些拱起的地面,一挖一个准。在霞光映红天空时,踩着夕阳而归,笋兜里都能满载而归,回家后,去皮,洗净,切片,放入腌菜,慢火细煮,要不了多久,清香便缭绕满整间屋子。顺着清香,嚼着冬笋,口舌皆酥,多少滋润了穷苦少吃的童年。
如今,时光不再,童年不再,鱼儿不再,蜻蜓不再,笋儿不再,童趣也荡然无存,只能把这些过往的记忆,珍藏在柔软的心底,偶尔品味,也能快乐如斯。
“如果我告诉你们,我很会爬树,你们相信吗?”
是个美丽的星期天,三位因音乐而结缘的朋友,约了共享一顿美食。其实美食是个借口,特别对我这已频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之列的人,但难得的相聚,且任情任性地敞开心怀,天南地北地聊个痛快吧!
话题从最近几场演唱会扯开,不知怎么忽然跳到童年时光。那么遥远遥远的场景,贞和梅兴奋万分地谈她们共同的家乡——马来西亚。两人是透过我而认识的。一直认为对方是台湾人,而且是我这类台湾的外省人。直到这刻。
顷刻间,浓浓的乡情把她们两人的兴致抬得好高,让我这介绍人也感染了喜气。静静地聆听她们的童年往事。长得白皙秀美的贞,儿时却是个常和男生争吵打架的Tom Boy:“个子高,每天在外面玩球,晒得又黑又粗……完全不像个女孩子。”是八年的英国留学生活,将这成长于马来西亚小镇的纯朴姑娘,培育成了典型的城市淑女。
同样高挑秀雅的梅,举手投足比贞更多几分帅气,是近年不时谈心谈艺的好友。与她在音乐欣赏的品味上,常有不期而遇的共鸣,为之惊喜不已。她当年中学毕业,自马来西亚赴台湾读大学,受教于K。三十多年前我们迁居新加坡不久,就与梅照过面。或许因我这“师母”的身份,是层难以穿越的墙吧,尽管早已相识,却要等到多年后,才因音乐剧《歌中情》而成知音。真合了那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梅兴味淋漓地描绘,儿时在马来西亚东海岸乡间的趣事,爬树,捉鱼,偷摘树上水果,被主人追骂等等。骤然间,我的童年也如梦如幻地回到脑际,忍不住打断她说:“如果我告诉你们,我很会爬树,你们相信吗?”“不相信”,两人异口同声。
在树梢头筑梦,游荡的日子,是生命中最初始的快乐源头。从南京来到台湾,战争和逃难的梦魇远去,家已安安稳稳地坐落在台中大肚乡福利新村。一片绿树覆盖满村,而那枝桠相缠的行道树,更让七岁的我练就一身轻功。每天从自家门前出来,先把鞋子脱了,放进书包,爬上第一株树,然后顺着交缠的一枝一桠往前攀爬,直到校门口那株老榕树。轻轻跳下来,把鞋子穿好,书包背妥,乖乖地做那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有两次未及下树,就被校长发现,厉声斥骂:“是哪位同学在树上?赶快下来,再不下来,上去捉你。”尽管心惊胆跳,却硬是屏住气息隐入绿叶丛中,躲过去了。
爬树是每个乡下孩子玩不厌的游戏,也是我这辈子惟一及格的运动。许多许多年后,曾在接受电台访问时,脱口而出:我希望自己是一棵树。因为树上的世界是想象的梦土,是无病无忧的乐园,让童稚的心灵在摇晃的绿影中,忘却家中缠绵病榻的父亲和妹妹。
“一直到今天,一看着树,我就不自觉想,该怎么一步步攀爬上去。”
“那么,你现在还会爬树吗?”
还爬得上树吗?望着窗外浓郁树影,我问自己。(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