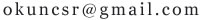整体上看,张爱玲的意象体系完全树立在日常生活世界(主要是女性生活空间),她的意象结构因而散射着更多的女性意识。尽管如此,由于作家具有平等审视世俗男女的宽阔视野,她笔下的男与女呈现明显的协商、互动关系,致使男性形象同样涵容于意象叙事,获得审美张力的贯透。张爱玲笔下的意象群具有很大的原创性。从范围上看,它几乎遍布日常生活的各种寻常物像:“蛀空了的牙齿”、泪珠、痣、手势,衣饰、镜子、茶具、花瓶、首饰、锅、破鞋、刀子、烟盒,玫瑰花、蝴蝶、鸟、曲蟮、月亮、太阳……这个意象世界五光十色、林林总总,从肢体、日用品到花鸟虫鱼,再到自然景象,反映了张爱玲意象营构的摄取宽度。杨义认为,“意象作为审美单体,具有超越时空的特性。意象一旦成为一篇小说的结构焦点,就可能产生对时空顺序灵活剪接的审美效应。随着意象的多重意蕴以不同方式渐次显现,小说的时空结构便会呈现前后错综、正反并置、或多维聚合等多种形态。”具体而言,对于张爱玲的意象叙事,上述意象的超时空性、结构性与审美性也不同深度地得到映现。意象叙事是张爱玲日常生活叙事趋向生命攀升的一种结构体制。从扩大文本“艺术至境”的层面看,意象叙事的形态与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作品高潮或结局等关键时刻的意象冻结,可以激活人类集体无意识层的记忆表象,将“女性形象——空洞能指”(孟悦、戴锦华语)转变成语言“雕刻”,逼近人类(女性)的永恒处境与生命“原型”。此种意象系列具有“物化苍凉”(许子东语)的审美境界。其中,“绣在屏风上的鸟”、“钉死的蝴蝶”、“苍凉的手势”……是这一类意象中最为典型的例子。《茉莉香片》中,“屏风上的鸟”出现在传庆的意识流动中,一方面传庆借用一个“定格”的物像压缩了母亲一生的命运图式,另一方面,“屏风上又添上了一只鸟”的意象又前后错综地交织起母子命运轮回的生命怪圈——母亲的悲剧刚刚褪色,可是“在他母亲心里的一把刀”,却又阴魂不散地在传庆的“心里绞动了”(《茉莉香片》)。透过“屏风上的鸟”这种多维聚合型意象,传庆母子的命运图式变得越来越哲理化、抽象化,从中既可看到葛薇龙、孟烟鹂、范柳原、佟振保们命运的影子,又可看到作家对整个日常生活悲剧性的生命诠释,广而言之,这个意象甚至具有涵盖整个人类生命史的色彩,只是那屏风是不自由,鸟象征自由。正如《浮出历史地表》一书所评论的,“‘绣在屏风上的鸟’,是张爱玲叙境中的核心隐喻。……这与其说是一个关于飞翔与逃遁的意象,不如说是一个关于死亡与囚禁的意象。”
其二,张爱玲意象叙事能够凝固人的心理意绪,它既可构成小说的结构焦点,又能将文本中人物人格心理的分裂性类型化,完成人性普遍指涉的功能。《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玫瑰花意象最为典型。小说中,红玫瑰与白玫瑰象征伴随男人生命流程的两种女人类型。在以振保为叙述主体的“玫瑰之恋”中,振保与红玫瑰、白玫瑰分别发生了各自独立的人生故事,但是因为有玫瑰花意象作为小说的结构焦点,两个分离的叙事环在情感意绪层面构成了正反并置的矛盾体,借助内在的心理逻辑,张爱玲建构起文本的复调性与有机性。而从意象意蕴上看,“红玫瑰与白玫瑰”意象深层次地隐喻了男人(其实也可以包括女人)在情感(婚姻)选择上的困惑。正如文中所说的,“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红玫瑰与白玫瑰》)因为这种生命困惑本质上是一种人性衍生物,所以具有不可避免性,虽然振保的“玫瑰之恋”囿于个体原因不见得苍凉透骨,但张爱玲却在玫瑰花意象隐喻的情感世界中看到了深深的绝望。
其三,张爱玲“以实写虚”(王安忆语)的意象叙事,具有模糊外景与真实、人工与自然之间界线的倾向,在一种人文理念的泛化中,展示意象的陌生化、哲理化、悲剧化生命内涵。这样的意象包括曲蟮、白鸽子、月亮、太阳等。如《封锁》中的曲蟮意象。“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依据上下文语境与曲蟮意象自身的审美结构,曲蟮意象可以包含以下三重意蕴:一、比较下文在“封锁”——静止、切割的时空内,女作家展现人类生命爆出的风流浪漫的火花,曲蟮意象的动态性构成对人的存在状态的一种逆向书写,它利用运动的特性,反衬出存在的单向性、重复性与静止性,是生命僵化的写照。二、独立地看,曲蟮“没有完”地抽长、缩短,如同西西弗斯滚动石头一样内含一种深深的哲理意味。三、曲蟮的动态性将日常物象陌生化、生命化了,从而使寻常的电车轨道在特有的审美张力中艺术化为具有自足特征的审美对象。
其一,作品高潮或结局等关键时刻的意象冻结,可以激活人类集体无意识层的记忆表象,将“女性形象——空洞能指”(孟悦、戴锦华语)转变成语言“雕刻”,逼近人类(女性)的永恒处境与生命“原型”。此种意象系列具有“物化苍凉”(许子东语)的审美境界。其中,“绣在屏风上的鸟”、“钉死的蝴蝶”、“苍凉的手势”……是这一类意象中最为典型的例子。《茉莉香片》中,“屏风上的鸟”出现在传庆的意识流动中,一方面传庆借用一个“定格”的物像压缩了母亲一生的命运图式,另一方面,“屏风上又添上了一只鸟”的意象又前后错综地交织起母子命运轮回的生命怪圈——母亲的悲剧刚刚褪色,可是“在他母亲心里的一把刀”,却又阴魂不散地在传庆的“心里绞动了”(《茉莉香片》)。透过“屏风上的鸟”这种多维聚合型意象,传庆母子的命运图式变得越来越哲理化、抽象化,从中既可看到葛薇龙、孟烟鹂、范柳原、佟振保们命运的影子,又可看到作家对整个日常生活悲剧性的生命诠释,广而言之,这个意象甚至具有涵盖整个人类生命史的色彩,只是那屏风是不自由,鸟象征自由。正如《浮出历史地表》一书所评论的,“‘绣在屏风上的鸟’,是张爱玲叙境中的核心隐喻。……这与其说是一个关于飞翔与逃遁的意象,不如说是一个关于死亡与囚禁的意象。”
其二,张爱玲意象叙事能够凝固人的心理意绪,它既可构成小说的结构焦点,又能将文本中人物人格心理的分裂性类型化,完成人性普遍指涉的功能。《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玫瑰花意象最为典型。小说中,红玫瑰与白玫瑰象征伴随男人生命流程的两种女人类型。在以振保为叙述主体的“玫瑰之恋”中,振保与红玫瑰、白玫瑰分别发生了各自独立的人生故事,但是因为有玫瑰花意象作为小说的结构焦点,两个分离的叙事环在情感意绪层面构成了正反并置的矛盾体,借助内在的心理逻辑,张爱玲建构起文本的复调性与有机性。而从意象意蕴上看,“红玫瑰与白玫瑰”意象深层次地隐喻了男人(其实也可以包括女人)在情感(婚姻)选择上的困惑。正如文中所说的,“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红玫瑰与白玫瑰》)因为这种生命困惑本质上是一种人性衍生物,所以具有不可避免性,虽然振保的“玫瑰之恋”囿于个体原因不见得苍凉透骨,但张爱玲却在玫瑰花意象隐喻的情感世界中看到了深深的绝望。
其三,张爱玲“以实写虚”(王安忆语)的意象叙事,具有模糊外景与真实、人工与自然之间界线的倾向,在一种人文理念的泛化中,展示意象的陌生化、哲理化、悲剧化生命内涵。这样的意象包括曲蟮、白鸽子、月亮、太阳等。如《封锁》中的曲蟮意象。“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依据上下文语境与曲蟮意象自身的审美结构,曲蟮意象可以包含以下三重意蕴:一、比较下文在“封锁”——静止、切割的时空内,女作家展现人类生命爆出的风流浪漫的火花,曲蟮意象的动态性构成对人的存在状态的一种逆向书写,它利用运动的特性,反衬出存在的单向性、重复性与静止性,是生命僵化的写照。二、独立地看,曲蟮“没有完”地抽长、缩短,如同西西弗斯滚动石头一样内含一种深深的哲理意味。三、曲蟮的动态性将日常物象陌生化、生命化了,从而使寻常的电车轨道在特有的审美张力中艺术化为具有自足特征的审美对象。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无其他回答
相似回答
大家正在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