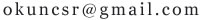审美理想:审美理想首先是一种理想,但又不同于一般理想的概念,它是人们有了一定的审美经验,审美习惯后的形成的美的生活与美的人的观念,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并随着社会的反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
是指人向往和追求的美的最好最高的境界。它是在审美经验的基础上产生,并是这种经验的高度概括。审美理想产生于社会实践中,人的全部社会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断地认识现实、产生理想,并实现理想的过程。人的审美理想就产生于这个过程中。作为审美经验的结晶与升华,审美理想与一般的社会理想、观念又有所不同,而且有经验性的形象特征,非逻辑概念所能函盖或替代,但是,要充分表现审美理想,使审美理想“物质化”,变成任何其他人都可以接受的东西,那就只有借助于透视审美理想的棱镜来反映现实的艺术才能做到。艺术作品对现实的反映是一种以审美理想为媒介的认识,因此,它比现实美更高、更集中,更典型。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大体上决定了艺术作品的倾向性和艺术方法、内容与形式。
审美理想是相对的,具有可变性。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审美理想表现的不仅是个别人的直觉趣味,而且是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阶级的审美关系的实践,因而它所概括的审美感知和审美体验的经验比审美趣味来得更为深刻、自觉、广泛,更鲜明地显示着一定时代、阶级的历史必然的理性要求。这使审美理想与一定的世界观、社会制度和实践要求密切相关,并在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而最终被决定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在阶级社会里,审美理想尤其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各时代、各阶级有其自身的审美理想,从而形成一定时代的审美趣味与风尚。审美理想还同时有历史继承性和共同性。每个时代的审美理想都是从漫长的人类审美意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都带有历史的痕迹。由于历史地形成的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各个民族的审美理想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形成了一个民族共有的而区别于别的民族的鲜明的民族风格、特色。但同时各民族的审美理想又不可避免地有着客观的共同的要求,具有全人类的共同内容。审美理想渗透于审美感受之中,主宰着一个民族、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审美趣味、风尚和趋向。
审美理想把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把实现理想的目的与手段统一起来,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强大精神动力。它可以用来衡量和评价生活和艺术中的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的各种事物与现象,引导人的正视并揭露现实中的矛盾,鼓舞人的不畏艰难,为光明的未来奋斗、拼搏。
论审美
www.8dou.net 【2005-6-8 20:42:00】冷草
本文旨在谈论文学审美,在此之前,我想先谈一谈想象和文学想象。
想象和现实永远是一对矛盾。现实中没有的东西(或者个人现实生活里没有的东西),人们才会去想象,来弥补现实的不足。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很穷,做梦也想发财(不是笑话,是事实),因而,我常常沉湎在钱财带给人的种种欢乐之中,并以此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前进的动力。那欢乐无疑只属于我的想象,不是事实——倘若是事实,我沉湎其中,则不是想象,而是回味了。固然,我没有的别人不一定没有,发财对我来说是想象的内容,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就是事实了,在一个个人飞速积敛财富的年代,发财的人肯定不少。我是出于羡慕和嫉妒,才把别人的现实移来作为自己想象的内容,并且希望自己也能仿效他们,过一过有钱人的生活。话说回来,钱财给人的欢乐,在我的经验中只能是想象,而不是现实。
文学的想象也属于人类的想象,和现实同样是一对永远的矛盾。文学的想象或许要借助现实场景,但它不会满足于现实。事实上,文学的想象是通过对现实的扬弃,努力建立一个与现实对应的理想世界。这个世界属于人的精神范畴。所以许多热爱文学的人说,文学是他们的精神乐园。一代代文学家为超越他们各自的现实而不懈努力,用他们的想象构造文学的世界,在文学想象的基础上建造出的文学世界,其实质是对现实的超越。
文学想象和人类其它想象不同。其中最大的区别,莫过于文学想象的非功利性。文学想象超越功利,带有鲜明的精神气质,是人类纯粹的精神追求。人类的一般性想象往往带有世俗欲望,文学的想象则类似人们常说的想入非非,所以弗洛依德称之为“白日梦”,弗氏的比喻并非贬意,而是夸大其辞地表达了文学和现实的悖离。
世俗者多认为文学想象不切合实际,但是,一个缺乏梦想的时代不是一个健康的时代,即便那梦想属于想入非非。
现实社会充满功利。功利既是人类以及人生的前进动力,也是对人自由的束缚。你如果把功利内容视为奋斗目标,也就意味认同它为一己之人生价值,你以为一旦实现了它,生活就呈现出意义,你的人生因此也有了价值。选择功利目标,同时意味放弃另外一些人生价值,比如说,自由。世上的事,得和失相辅相成。你要追求名利地位、荣华富贵,就必须牺牲许多有意义的东西。
我有一个观点,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先不去管它,但我坚信它对人类是非常有用的:
对自由的向往,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秉性。自由是人类生命最有价值的价值,所以也是个人最有价值的价值。你选择了功利,就表示你心甘情愿接受它对你的束缚,同时也意味放弃更有价值的自由。在人类的语汇中,自由和束缚从来是一对反义词,它们的意义,能从对方那儿去寻找--什么是自由?自由是摆脱束缚;什么是束缚?束缚是不让人自由。功利和自由,对人生而言,两者只能取其一。
我宁愿我的观点符合现实,而不是对人类的美化。
前面说过,文学的想象和现实是一对永远的矛盾。矛盾的焦点,最终落实在功利与否上。文学从本质上说是非功利的,而现实从本质上说是功利的。它们分别代表了人类超越现实的渴望和世俗人生的欲望。文学的意义在于摆脱现实束缚,超越现实,表现人类对自由的永恒追求。“摆脱现实的束缚”、“超越现实”、“对自由永恒的追求”,这一连串话语的意义前后贯连,层层递进,其中,“摆脱现实束缚”是“超越现实”的前提,而“对自由永恒的追求”则是“超越现实”的动因与结果。它们不可或缺,剥离其中任何一句,表达的意思就不完整了。
当然,世上也有功利的文学。文学用它的形象,用它的情感打动人。于是,有人就利用这一点,让它为自己的功利服务。而文学恰好又有这方面的功能,能够满足他的需要。文学是可以功利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文学根据阶级来划分文学,文学可以分为无产阶级文学、资产阶级文学,或者其它什么阶级的文学。文学其实是泛人类的,把泛人类的文学划入不同的阶级,就是功利。文学可以功利,但功利不等于文学。事实证明,那些功利性强的文学作品,尽管可能在当时产生一定的轰动,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在文学历史长河中无法长久生存,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还没出现过既十分功利又流传千古的经典作品。文学从根本上说是超功利的,功利不是真正的文学。
文学有许多属性,其中最能体现它超功利性质的,莫过于审美。我之所以那么说,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文学创造美。文学作品的最终目的必然是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审美是文学最基本的属性,在文学作品中具有普遍意义。读者阅读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不可能没有审美感受,而读者阅读任何文学作品,其初衷十有八九是为了获取美的享受。
其次,人类的审美本身超越功利。审美是一种行为,它有一个主体,一个客体,审美的行为,是主体感受客体,主客体之间的交流。有人说,审美需要距离,主体只有同客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进入审美状态。这话说得不错。审美主体之所以要同审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是为了减弱对它可能持有的功利观,他没有了功利观,才能真正进入审美状态。小说描写的满汉全席同餐馆里的满汉全席意义不同,小说里的满汉全席不可能满足你的口腹之欲,对你而言,它们是两种不同的“风味”。
审美是纯粹精神的内容。人类的感情通过审美得到升华。文学有了审美,才有感染人的力量。审美在文学中的意义不能低估。我认为它是文学的核心内容,奠定了文学的根本意义。文学作品功利性的内容不可能带给读者真正的审美感受;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不管作者创作初衷如何,也不管理论家如何评论,都不可能不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古今中外有许多关于美的定义。谈论美是什么,它究竟属于主观或者客观,那是美学家的事。在文学范围内,理解什么是审美,或许比理解什么是美更有意义,虽然审美离不开美,理论上后者的意义先于前者。
动态地看文学,它由两个过程构成,一个是创作,另一个是阅读。无论作品的创作过程还是阅读过程,都同个人有关,前者离不开作者,后者离不开读者,个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文学是人的行为,离开了人,也就没有文学。审美同样如此,也是人的主体行为,是主体对审美对象的感受,离开了人,也就没有了审美。在文学范围内,不可能存在脱离审美的美。作者把自己的审美感受表现在作品中,而读者则从作品内容中获得审美感受。
前面说过,想要进入审美状态,审美的主客体之间必须保持一定距离,对此我深有体会。
我喜欢旅游。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出去走走,走出都市,看看高山大川,湖光山色,小镇风情。我经常一个人坐在山顶或者海边,面对一望无际的自然,呆呆出神,一坐就是数个小时。我到过不少地方。旅游让我心情愉快。旅游途中,我总能忘却自己正在过的世俗生活,而用旅游者的目光审视我所看到的人、事、物,把他(它)们统统当作我的欣赏对象。毫无疑问,那是审美的体验。
后来,我发现一个异常情况。每次我回到家,走出车站,面对自己生活的都市,总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哪怕我昨天才离开,甚至今天早晨才离开;我在那都市生活了许多年,对它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它的许多偏僻小路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可偏偏就在我步出车站的那一瞬间,它对我显得既熟悉,又陌生,我内心涌动着莫名的兴奋之情。那感觉要过一些时间才慢慢消失。
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吗?许多人可能也有过类似感受。我琢磨它是怎么回事。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刚下火车时,还沉浸在旅游的心境中,便把那都市看成自己下一个旅游点,是心理的惯性导致了心境的移位。旅游,穿行于不同地点,不断改变自己的空间位置,我同那都市有了空间上的距离,于是拉长了时间上的距离。所以,当我再次见到它时,便有了恍若隔世的错觉,人也变得兴奋起来了。它其实就是审美,由于时间的距离而产生的审美,如同我们对往事的回忆,因为有了时间的隔阂,无论悲伤或者欢欣,都成了审美内容。
有一回去北方,将近一个月时间,回来时,我脸色黧黑,风尘仆仆。车站聚了许多揽客者,手上捧个牌子,写着“住宿”两字。其中一个见了我,以为我初来乍到,问我,要不要旅馆?我觉得意外,也感到有趣,没想到离家才一个月,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就变成了域外之客。那是我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了,但它给我的印象却特别深。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有它的象征意义:刚下火车的我,无论是外观还是心态,都还延续观光的状态,同那都市保持相当的距离。
想获得审美感受,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距离最好不即不离,远了看不清,近了未免功利。当然,有距离不一定就有审美。距离是审美的前提,而不是过程,更不是结果。审美的意义不是来自主客体之间的距离,而是来自它们之间的交流。保持距离,是为了让主体能更好地审视对象。主体一旦进入审美状态,先前的距离感自然消失,最终和客体融合在一起。在进入审美状态前,主体和客体必须保持距离,进入审美状态后,两者之间就不存在距离了。距离的存在使审美主体在“物”的层面对审美对象不再怀有功利,距离的消失则使得审美主体超越“物”的层面,在精神上同审美对象融为一体。
李白有两句诗,“坐望敬亭山,相看两不厌”,形容了物我两忘的审美状态。诗人和敬亭山存在空间上的距离,他不是它的主人,它也不能给他带来任何物质利益。他远眺它,时间一久,它在他眼里似乎活动起来,也如同他那般久久凝视对方。此时此刻,他已经感觉不到彼此间距离的存在。此山即此人,此人即此山,山的精神即人的精神。
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一文中写道:他仕途受挫,被贬到了永州,想通过游山玩水来排遣心情;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西山,他登上西山顶上后,视野骤然开阔,心胸也豁然开朗起来,周围的景色都在自己脚下,一直铺展到天边,西山特立高耸,气势非凡,他沉湎其中,忘记了回家的时间。柳宗元是这样描写他当时心情的:“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文章最后,柳宗元深切体会到,自己从前虽然去过不少山水,但那都算不上真正的旅游,只有游罢西山,才明白旅游山水的意义,于是给文章起名为“始得”。
柳文的描述,可以作为任何一部美学著述谈论审美时援引的事例。文章写了现实对他心情的影响,写他如何通过游西山,摆脱了现实的阴影,最终超越现实,他的心灵、精神和大自然(此处的大自然即为作者的审美对象)融为一体,在物我两忘的审美状态中,达到心灵的自由,达到了人的自由。那是心灵的游历。西山的特立高耸,象征他所仰慕的精神风范和人格追求。
儒和道是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两个思想流派,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它们起源于二千多年前的百家争鸣时代,对二千多年来的中国文学不可能没有影响。儒学的人生观是入世的,它对人生的看法自然影响了它对文学的看法。《论语•阳货》中有一段话:“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从中能看出儒家的文学观带有鲜明的社会功利性。道家的人生观与之相反,是出世的,它倡导返朴归真,回归自然。返朴归真和回归自然意味着对世俗人生的超越,而这恰好同人类的审美态度一致。
从表面看,道家对文学的重视程度,似乎远不及儒家。儒家的经典著述,比如《论语》,其中有一些直接谈论文学的句子或者段落,但在道家的经典,例如《老子》或者《庄子》里,相关内容很少出现,纵然有,也只是片言只语,而且往往带有否定性。面对同一个对象,一个迫切要去干预它,让它为自己服务,另一个却摆出事不关己的姿态,不急不慢,不温不火,同它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两种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种文学观的区别,即功利的和非功利的。如果把文学本身视为一个审美对象,那么道家对待它的态度似乎更符合它的原意,也就是,道家是用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审美的文学。道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在于理论指导,而在于精神。“道可道,非常道。”谈论文学如何如何有意义,或许已经远离了它的真实意义,关键要“得鱼忘筌”,“得意忘言”,“鱼”和“意”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古希腊学者论述美,有所谓“崇高”、“优美”之分。“崇高”和“优美”,属于审美内容的风格。美的内涵包容广泛,我个人认为,在人类眼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含有美。山川草木,日月星辰,人格追求,理想追求,人性的美好,以及人世间大悲大喜的事件--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澄江静如练”是美,“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是美,“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是美,“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是美,“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是美,“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也是美。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寥寥数语,写景,咏古和感怀交织在一起,创造出时空飘渺悠远的诗境,那诗境由于诗人形象的衬托,更具有悠长的韵味。
苏轼在《前赤壁赋》里,描绘了一个能够洗去人世间种种烦恼的澄澈空明的天地:
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世人常把真、善和美视为三种不同的对象来论述,这并不妥当,因为它们不具备逻辑上的并列关系。真有美的内容,善也是如此,它们相互交融。真与善,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美好内容,因而都能成为人的审美对象。文学的核心是审美,但文学不可能不关注人世间的真与善,因而真与善不可能不成为文学审美的内容。真正的文学家,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从来都是用美来包容真与善。美即真,也是善。
科学崇尚真,文学崇尚美。有人把两者视为科学和文学的区别,其实不然。真正的科学也有美,而真正的文学又岂能忽视真?文学也崇尚真。但文学崇尚的真实不同于物理的真实、细节的真实和表象的真实,而是事物内在的真实。事物内在的真实是人世间和宇宙天地的大真。对事物内在真实的揭示,对天地人生之大真的揭示,是审美。卡夫卡的小说用扭曲现实的手段表达真实,成为文学审美的经典之作。
文学对真实的揭示离不开形象,它通过形象来把握真实。文学撇开了逻辑的细密推理,而凭直觉来感悟对象。逻辑推理和直觉感悟,是科学和文学在揭示事物真实过程中运用的两种不同手段和思维方式。这是文学和科学的不同之处。不同的思维方式感受到不同的真实,一类是审美的真实,另一类则是科学的真实。当然,科学对事物规律的揭示,也能进入审美状态。陈省身说,自己之所以喜欢数学,是因为它的美。科学家若能进入审美状态,则是最高的境界。
善和美的关系也是如此,善中有美,但不全是美。善属于道德范畴,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善的对立面是恶。我们在语言习惯上,总是把善和美连在一起,似乎有了善,也就有了美。汉语有“美好”一词,似乎美的就是好的,好的也是美的,美和好不能分离。语言是人的思维形式,语言的习惯也就是人思维的习惯,在我们的思维习惯里,美和善并不分离。
当然,美和善不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说法。善是善,美是美,它们有不同内涵。善固然包含美,但不全是美。属于人类社会一般性道德原则的善,例如友情,亲情,正直,诚实,善良,高尚——其中包含美的内容,属于人性之美。道德还有它的相对性,不同时代和民族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古希腊崇尚人体的健美,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手必须全裸,在伊斯兰国家,裸露身体被认为有伤风化,就成了丑陋的事了;中国古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是维持封建社会秩序的道德原则,延续数千年,但在现代人眼里,它是造成人与人不平等的罪恶渊薮。
区别美和善,只要看它们是否功利就行了。善是价值观,无疑有功利色彩,倘若它超越功利,就能转化成审美对象。因此,同为人生追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价值观属于善,而“岁寒然后知松柏后凋”的价值观却是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是善,而“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则洋溢着人生的悲壮之美。
美包容广泛,真正感动人的,应该是那些体现人类审美精神的内容。这句话听上去像在绕圈子,其实不然,美的内容有可能存在于审美之先,但美的价值只能产生于审美之后,换句话说,美的内涵只有当它成为审美对象,才有价值。
审美对人类而言意义非凡。没有了审美的愉悦,很难想象人类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当然,愉悦也不是审美的目的,它只是审美的效果。而且,审美的效果也不全是愉悦,丑不带给人愉悦,但同样能成为审美内容。《悲惨世界》的卡西莫多,庄子散文中一系列有生理残缺的人物,都是文学作品的审美内容;“惊栗”是古希腊学者谈论悲剧审美时经常用的一个术语,人的“惊栗”和轻松愉悦,恰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因此,除了带给人精神上的愉悦,人类的审美还应该有其它意义。如果要我来回答审美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或者对它下一个简单的定义,那么我会说:
审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精神追求,在它身上,集中体现了人类对超越现实的渴望和对自由的向往。
列子御风而行,泠而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庄子•逍遥游》
作者借神话人物表达了超然物外的意趣和人生的永恒追求。人生也还有其它追求,例如儒家理想人物尧和舜的所作所为,但同藐姑射山上的神人相比,他们只是尘垢秕糠。
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由是人类的永恒追求。超越和自由体现了人类审美的精神特点,也是它形而上的意义。审美把现实理想化,并且永远期待理想的现实化。反观人类历史进程,一代代人为了摆脱现实的束缚所做的种种努力,以及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既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行,又赋予人类以精神上的意义——一种渴望超越现实的精神,其本身却成为现实人类的精神风貌。超越和自由是人类代代相传并且持久不灭的精神追求。美的内容,当它成为人的观照对象后,总能够表现人类超越现实的渴望和对自由的向往,唯其如此,它才感动人。类似的表现或多或少,或隐或显,但不能没有。西山的特立高耸固然先于柳宗元存在,但只有当它在柳宗元眼里成为人格的化身,才具有审美价值。
审美理想与艺术的历史生成
所属栏目 > 审美的镜子
作者:谭好哲 发布时间:2003-6-2 10:32:51 点击数:1640
[发表评论] [关闭窗口]
1
审美理想是人们对社会审美经验的概括和升华,同时也是对社会审美需要和审美利益的反映。因此,审美理想与社会的各种理想和价值观念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而存在的。审美理想存在于人们的主观意识之中,具有审美的普遍性,是人们在审美活动中鉴别和创造的最高尺度、最高标准。同时,它又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中,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并在社会历史实践的影响下不断发展。因此,审美理想不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集团和阶级都存在着统一的审美理想,不仅不同时代的人们具有不同的审美理想,而且同一时代不同阶级、不同集团的人们在审美理想上也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由于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能像在艺术的创造与欣赏中那样充分地表现出和感受到审美理想,因而在审美理想的对象化、现实化过程中,艺术便起着重要作用。审美理想和现实的统一,首先在艺术中充分表现了出来。
2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审美理想大多数仅仅停留在、表现在艺术阶段,艺术被视为审美理想的一种物化形态,是进行审美教育的最重要的工具。这一点,在德国古典美学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德国古典美学家们都认为“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然而不论是康德、席勒、谢林还是黑格尔都是将审美囿限于或主要局限于艺术领域。在他们的逻辑中,审美的解放性质基于审美的自由性,而审美的自由性又是以审美活动与科学认识活动和道德实践活动相分离为基础和条件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像从前的美学家那样把人类的审美活动局限于艺术活动或者是精神劳动,而是认为审美涉及到人类的一切活动,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物体是人类活动的根本标志之一。因此,马恩的审美理想就不是一般的艺术理想,也不是建立在精神太空中的美学理想,而是将审美看成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审美活动是整个人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马恩的审美理想是与他们的社会理想紧密相联的。把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联结起来的纽带就是理想的实践性质,即在社会实践中,审美理想具有社会意义,社会理想具有审美意义,社会意义与审美意义辩证统一。
3
我们知道,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因而在没有人的生产和人类出现以前,没有作为美而单独存在的东西。歌德说过:“我们不知道有不存在人类关系的世界,我们也不希望有不打上这种关系印记的艺术。”《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3—94页。这是一个极精彩极深刻的说法。马克思在《手稿》中也说了同样意思的话:“但是,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本,第131页。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离开由实践活动所构成的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美和美的意识都是不存在的。只是在有了生产劳动,有了“人化了的自然界”作为人的“创造物”或作品之后,自然界才具有了审美属性,美才出现。因此,美不在别的地方,就在“人的对象化”的劳动过程中,就在“人化了的自然界”中。在人类历史的原始阶段,美与善是同一的,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与实用关系也是同一的。原始人用来劳作的磨光的石刀石斧和刻削的棍棒及其装饰物既是有用的,又是美观的;狩猎民族的猎获物和农耕民族的耕作物既是维持生命的生活资料,又是赏心悦目的审美对象
参考资料: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2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审美理想大多数仅仅停留在、表现在艺术阶段,艺术被视为审美理想的一种物化形态,是进行审美教育的最重要的工具。这一点,在德国古典美学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德国古典美学家们都认为“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然而不论是康德、席勒、谢林还是黑格尔都是将审美囿限于或主要局限于艺术领域。在他们的逻辑中,审美的解放性质基于审美的自由性,而审美的自由性又是以审美活动与科学认识活动和道德实践活动相分离为基础和条件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像从前的美学家那样把人类的审美活动局限于艺术活动或者是精神劳动,而是认为审美涉及到人类的一切活动,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物体是人类活动的根本标志之一。因此,马恩的审美理想就不是一般的艺术理想,也不是建立在精神太空中的美学理想,而是将审美看成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审美活动是整个人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马恩的审美理想是与他们的社会理想紧密相联的。把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联结起来的纽带就是理想的实践性质,即在社会实践中,审美理想具有社会意义,社会理想具有审美意义,社会意义与审美意义辩证统一。
3
我们知道,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因而在没有人的生产和人类出现以前,没有作为美而单独存在的东西。歌德说过:“我们不知道有不存在人类关系的世界,我们也不希望有不打上这种关系印记的艺术。”《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3—94页。这是一个极精彩极深刻的说法。马克思在《手稿》中也说了同样意思的话:“但是,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本,第131页。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离开由实践活动所构成的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美和美的意识都是不存在的。只是在有了生产劳动,有了“人化了的自然界”作为人的“创造物”或作品之后,自然界才具有了审美属性,美才出现。因此,美不在别的地方,就在“人的对象化”的劳动过程中,就在“人化了的自然界”中。在人类历史的原始阶段,美与善是同一的,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与实用关系也是同一的。原始人用来劳作的磨光的石刀石斧和刻削的棍棒及其装饰物既是有用的,又是美观的;狩猎民族的猎获物和农耕民族的耕作物既是维持生命的生活资料,又是赏心悦目的审美对象。从汉字“美”的词源学意义上考察,可以很清楚地明白这一点。许慎《说文解字》释“美”字曰:“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徐铉注道:“羊大则美,故从大。”在古人看来,肥大的羊儿能供给人可口的膳食,所以是美的。而作为六畜之一的羊,无论是其捕猎或是其驯养都是人的劳作的具体表现。羊是这样,其他的动植物当然也是如此。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95页。
4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正是随着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人类才与对象世界建立起了不同于意志实践和理论认识活动的审美关系,才能够从经由实践改造了的“人化了的自然界”中欣赏到美,而且逐渐发展到与客体中未经改造的自然发生认识关系、审美关系,太阳、月亮、崇山、大海等自然物中存在着的美的属性的潜能为人们所认识、发现、观赏;同时,人类的生产实践日益扩大着客体的范围,使客观实在中原来与人没有发生关系的事物发生了认识关系甚至实践关系,这也就使客观实在中潜在的美转化为现实的美,或者说使自然中与人构成审美关系的可能性的条件转化为现实性的条件,美日益丰富多样起来。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看来,美是客观的,但这只是就美的存在物独立于认识和欣赏的主体(即人)的主观意识之外这一点而言的,并不是说美作为客体的属性与实践活动的主体即人无关。美要作为现实的美,一定要跟人发生关系。只有在人作为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物,只有在人进行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以后,美才被创造出来、发展起来,人才从欣赏人化了的自然中的美,发展到欣赏客体性的美、自然世界的美。没有人的对象化,自然至多具有“美”的潜能罢了,而不可能成为美的对象,所以,“人的对象化”、“自然界的人化”是美的源泉,是人类审美生活得以形成的基础。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理解了马克思下述完全正确的论断:“劳动创造了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第46页。这一论断不仅准确、深刻地揭示和概括了美的根源,而且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进一步的结论,即从根本上说美的本质是与人的创造性劳动、与人在创造性劳动中所物化的本质力量相关的,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页。所以,离开生产实践去寻找美的根源,谈论美的本质,是不会取得理论认识上的真正收获的。
5
审美和艺术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消费和精神创造生活,均与人类社会赖以存续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说“劳动创造了美”的话,那么劳动同样也是艺术发生的根据。换言之,艺术也是作为社会的人在其劳动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创造。
原始文艺的产生是以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存在为前提的,而这种主、客观条件正是劳动实践的结果。生产劳动为人类自身创造了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之后人们才有了从事文艺及其他精神活动的客观可能性。劳动创造了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造成了自然的人化,这才有了艺术感知和艺术创作的客观对象。同时,劳动创造了人,使人的大脑日渐发达,人手及其他感觉器官日渐属人化,从而形成了人所特有的感受能力、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尤其是形式感、想象力和情感需要等等。这些“人类的高级属性”(马克思语),是文艺活动主体必须具备的创造能力,或者说是文艺产生的基本主体条件。劳动还创造了将人类文艺活动的主、客体因素有机统一起来的媒介材料——语言及其书写符号文字。语言不仅是文学的表现工具,也是艺术思维从而也是其他各种艺术创造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原始文艺多是带有功利性的,原始人与劳动生活相关的种种需要往往是原始文艺产生的直接动因。原始文艺或者直接产生于劳动过程之中,成为组织劳动(协调动作、鼓舞情绪、提高效率)的手段;或是摹仿和再现劳动生活的背景,作为交流和传授生产经验的一种方式;或是反映了劳动者祈望征服自然、取得劳作收获的情绪和愿望。中国古代的所谓“举重劝力之歌”和中、外的一些神话传说等,都表明了原始文艺与物质生产实践之间的相应关系。而且原始文艺的内容和形式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物质生产劳动的制约。
6
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客观方面来考察,生产技术的进步对艺术的产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技术,就是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中的生产工具以及运用工具的知识。技术进步是由生产实践的发展造成的,反过来它又推动了生产和整个人类生活的发展。我们知道,“文化”一词在英语(“culture”)和德语(“diekultur”)中都有耕作的意思,也就是指人类借助于工具支配自然物使之成为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因此,工具的进化就是人类智能进化和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人们以工具使用的类型来命名一个时代的特征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等等就说明了这一点。工具作为物质生产的必要手段,是生产的主客体之间的连接桥梁。人类通过工具进行生产,既改造着自然,也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改变着自己的器官尤其是手和头脑,因而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亦即技术的存在与进步不仅对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有重大意义,对艺术的起源和发展也有重大的意义。
技术对艺术起源的作用首先表现在一些新材料和新工具可以为艺术家直接运用。人类早期的艺术如绘画、雕刻、器乐的制造和弹奏以及制陶等等,都必须以工具的制造和熟练使用为前提。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即距今约200万年至二三十万年间的猿人阶段,人类已经能够通过直接打击的方法生产极为简单的粗糙的石制工具了。但工具的进步十分缓慢,直到旧石器时代中期,即距今约二三十万年至五万年间的古人阶段,考古学所发现的尼安德特人使用的“莫斯特工具”仍然是木矛、木棍和飞石,以及备用的大块燧石。这类工具当然是不能用以雕刻和绘画的。而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五万年到一万年前的真人阶段,工具有了相当大的改进,这时原始人有了薄如刀片锐利似锋刃的尖状石制工具,有了骨制鱼杈、矛头、针等等,并学会了使用黑、褐、红、黄、白诸色颜料,这就使原始人在岩壁上雕刻与绘画以及在骨器上进行浮雕和刻线具备了条件,成为可能。没有这种技术上的进步,原始的雕刻艺术和洞穴壁画的产生是难以想象的。
7
在探讨艺术起源问题时,人们往往比较注意原始人的生存条件和他们的物质生产实践对原始艺术的内容、特点等的决定和制约作用,而很少涉及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对原始人类的艺术感觉和想象能力的培养作用,其实这一方面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知道,无论是制造工具的劳动还是借助工具改造自然的劳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由马克思概括的这一劳动活动的特征,可以引申出两点结论性认识:第一,由于人在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和制造工具之前,就要考虑他的活动欲得到什么结果,达到什么目的,并在头脑中形成某种表象;而为了使头脑中的表象物化为现实的创造物,即获得预期的效果,实现先定的目的,又需要设想对物质对象的形式或外观应该进行何种程度的改变,应该采用何种技巧和手段,做何种努力,并规定这种努力的步骤、阶段、时限等等,这一切无疑会慢慢地间接培养起人的想象能力。第二,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也间接培养了人的艺术感觉,尤其是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人对形式美的感受和追求的能力。如上所述,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培养了人的一种特殊的心理能力,即预先在内心形成加工对象的“表象”或模式,并以这种“表象”或模式规定自己的劳动方向,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在漫长的工具制造和使用过程中,人便逐渐地获得了对事物形式的巨大敏感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了独立的形式美感。这一点,已得到许多史前艺术专家的肯定。如美国一位重要的人类学家佛朗兹·博厄斯在其《原始艺术》一书中就以大量的艺术实例证明说,艺术形式并非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它多半得力于工具的熟练操作,形式感觉本身多半是技术经验的产物。像直线、平面、圆圈和螺旋一类作为图案要素而出现于各种制品上的规则曲线,在自然界中并不多见,因而人脑中也不会构思这类形态,它们大多起于工具的熟练运用。所以,形式感觉虽然有一部分起于对自然物和人体的观察,但艺术却多半得力于由掌握技巧发展起的对形式规律的反应。
8
在国内外理论界,有一个与艺术起源问题密切相关的争论,即审美和艺术孰先孰后的问题。有一些理论家认为艺术起源于对美的追求,也就是说美感产生于艺术之前,并作为推动艺术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居先存在。与此相反,另一些理论家则认为艺术在起源时其实是与美无关的,人类不是先有了审美能力而后才有了追求美的艺术,实是先有了艺术而后才相应地培养了审美能力。应该怎样看待这种争论呢?
无论说先有了审美才有艺术还是先有了艺术才有审美,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从历史发展来看,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精神性活动,审美和艺术都有一个萌芽期,都是在人类的劳动实践中从人对现实的功利关系中逐渐演化出来的。从活动主体看,二者都有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渐进过程,而且二者的演化与渐进过程基本上是同步的。诚然,人类在创造第一部艺术作品之前还不具备纯粹独立的审美要求,在当时原始的生活条件下和自然环境中,人们还谈不上有纯审美的要求,人们的审美感受能力也肯定是非常薄弱的,因而艺术的产生不可能仅是为了满足审美的要求。正如希尔恩所说的,“在第一次的艺术作品被创造以前,艺术的冲动和艺术的感觉必然处于非常不发达的状态。在它们被实现于某些客观作品之前,审美的要求不可能达到它自觉的目的。”所以,不能把艺术归结为对美的追求的结果,不能得出审美先于艺术的结论。但是由此也不能得出艺术先于审美的结论。因为如果说当时人们的审美感受力还是薄弱的,审美的要求还没有达到自觉目的的话,那么,当时人们的艺术感觉能力同样也是薄弱的,创作的冲动同样是不自觉的。而且仅就理论本身的角度看,也不能从人们在创作第一部艺术作品时审美的要求还不自觉,就证明当时的生活中不存在着审美因素。
人为地规定审美和艺术孰先孰后,一个根本缺陷或者说失足之处就在于割裂了审美生活和艺术生活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原始人类那里,实践活动的成果——猎获的猛兽、驯养的牛羊、耕种的作物、精致的工具以及工具上的装饰等等,这些首先作为功利对象而存在的东西既是审美对象又是艺术对象,它们既培养了人们的审美能力,也培养了人们的艺术感受能力。所以,正确地说,在审美生活和艺术生活长时期的“萌芽状态”期间,二者的范围是同样宽广的,都与物质生产有着难解难分之缘,很难加以明确区分。原始人并不存在一个特殊的审美活动领域,也不存在一种专门的艺术活动领域。作为分工的一个特殊领域的艺术活动,职业艺术家的出现,是在人类踏进文明的门槛亦即形成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分工之后才确立和发展起来的。艺术活动一旦从物质生产中独立出来,同时也就标志着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确立,从此人类的审美活动才有了一个特殊的专门的领域——艺术领域。这之前,人类的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都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中的审美和艺术活动,是同原始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以及原始人以前逻辑的拟人化幻想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原始意识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与人类今天正在从事的审美和艺术活动是不能同样看待的。所以,审美和艺术的先后论,不仅不符合原始文艺的实际,也掩盖了文艺起源的真正根源
参考资料: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965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审美理想是在人们美的创造中和人的实践中形成的。
什么是审美理想?审美理想是如何形成的?具有什么意义?请结合现实生活谈谈...
审美理想产生于社会实践中,人的全部社会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断地认识现实、产生理想,并实现理想的过程。人的审美理想就产生于这个过程中。作为审美经验的结晶与升华,审美理想与一般的社会理想、观念又有所不同,而且有经验性的形象特征,非逻辑概念所能函盖或替代,但是,要充分表现审美理想,使审美理想“物质化...
什么是审美理想?审美理想是如何形成的?具有什么意义?请结合现实生活谈谈...
我认为理想就是自己争求的目标,努力的方向。我自幼生长在农村。当时看到小学校的老师很受到村里人的尊敬,在小孩子们的面前也很有权威,所以当时的理想就想当教师。在新中国成立初,百废待兴,人才缺乏。我初中毕业时,学校有分配毕业生当教师的任务,我就积极报名了。结果当时的班主任没批准,让我上...
什么是审美理想?审美理想是如何形成的?具有什么意义?请结合现实生活谈谈...
1. 审美理想是人们在审美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美好生活和人物的观念,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2. 审美理想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美的最高境界,它产生于社会实践中,与一定的世界观、社会制度和实践要求密切相关。3. 审美理想是相对的,具有可变性,它反映了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阶级的审美关系的实践,比审...
何为审美理想,审美理想对社会美起什么作用. 审美理想
审美理想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它是人们认识现实、追求理想并实现理想的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理想不仅仅是个人趣味的体现,更是整个社会集团和阶级的审美实践的总结。审美理想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它与一定的世界观、社会制度和实践要求密切相关,并受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和时代...
何为审美理想,审美理想对社会美起什么作用. 审美理想
审美理想产生于社会实践中,人的全部社会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断地认识现实、产生理想,并实现理想的过程.人的审美理想就产生于这个过程中.作为审美经验的结晶与升华,审美理想与一般的社会理想、观念又有所不同,而且有经验性的形象特征,非逻辑概念所能函盖或替代,但是,要充分表现审美理想,使审美...
什么是审美观?
回答:辨别、领会事物的美。 审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指人与世界(社会和自然)形成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美,美是能够使人们感到愉悦的一切事物,它包括客观存在和主观存在。其次我们应该明确,审使人们对一切事物的美丑作出一个评判的过程。由此...
什么是理想?结合实际谈谈理想对于你的人生的的重要意义?
理想,是对未来事物的美好想象和希望,也比喻对某事物臻于最完善境界的观念。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有实现可能性的、对未来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向往和追求,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崇高的理想信念能够引导如何做人,人的理想信念,反映的自己是对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期望...
谈谈你所理解的审美理想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集团倾向性和人类共通性的统一,是文学审哭意识形态性的重要性质。 第二, 第二,从功能上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既是认识的,又是情感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无疑包含了对社会的认识,这就决定了文学有认识的因索。即使是那些自称是’‘反理性”的作品,也包含了对现实的认识,只是其认识...
文艺美学基本理论·审美理想
审美理想则是人对完整的、具体可感的、至善至美的境界的一种观念、规范和要求。在艺术中,审美理想能够获得最充分的体现,它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真、善、美的综合具象反映,具有个性与共性、经验的普遍性和历史的必然性相结合的特点。艺术作品对现实的反映是一种以审美理想为媒介的认识,因此,它比...
审美理想的介绍
审美理想是人们在自己民族的审美文化氛围里形成的,由个人的审美体验和人格境界所肯定的关于美的观念尺度和范型模式。审美理想产生于社会实践中,人的全部社会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断地认识现实、产生理想,并实现理想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