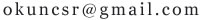哲学足以长久地令人惊奇。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古希腊人赋予了哲学一个独特的名称,把它叫作philosophia (注:为印刷方便,文中所引希腊文均据苗力天先生手订汉语拼音希腊字母对照表,以拉丁字母形式写出。该对照表见1999年《哲学译丛》第2期。),而哲学家相应地被叫做philosophos。philosophia由philos和sophia两部分构成,philos由动词philein而来,是philein的形容词形式,philein是动词,指“爱”,而sophia指“智慧”,从而,philosophia按其本义而言,乃是指“爱智慧”。如同sophos相应于sophia是指“智慧的人”一样,philosophos相应于philosophia,指“爱智者”。 “爱智慧”和“爱智者”分别道出了“哲学”和“哲学家”原初的意蕴,但这并不是最为原初的,至少,它仍然需要解释。据说,最早使用philosophia和philosophos的是毕达戈拉斯。狄奥根尼•拉尔修这样记载说:“据蓬托斯的赫拉克利德在《论无生物》中所说,当毕达戈拉斯在西库翁同西库翁或弗里阿西亚的僭主勒翁交谈时,他第一个使用了philosophia的名称,并且把他自己称作philosophos,因为除了神,没有一个人是智慧的。”[1](第1卷第12节)在别的地方,拉尔修还记载了有关毕达戈拉斯的一则轶事: “苏西克拉底在《师承录》中说,当弗里阿西亚的僭主勒翁问及他是什么人时,他说,‘一个philosophos’。他还说生活就象节日盛会,竞赛的来此,做生意的来此,而最好的观众也来此,同样,他说,在生活中,一些奴性的人生来是名利的猎手,而philosophos生来寻求真理。”[1](第8卷第8节)在这最后一句话中,一个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就是andrapodoodees。这是一个复合词,由andrapodon和eidos构成。andrapodon指奴隶,而eidos指形式、外观。从而andrapodoodees就指“具有奴隶本性的人”,也即“奴性的人”。毕达戈拉斯在这里显然是说:只有奴性的人才追求名和利,而哲学家追求真理。与此对立,他就明确地把哲学家归到了自由人的行列,从而相应地也就把自由和真理联系在了一起。这引导我们进一步深思哲学philosophia的更为原初的内涵。 “真理”一词希腊文写作aleetheia。这是一个复合词。a—是前缀,表否定。leetheia由动词leethein而来,leethein是动词lanthanein的古体。lanthanein意为“隐蔽”、“不被注意”、“不被看见”。由此,真理aleetheia在本义上通常被解作“去蔽”,也就是去除遮蔽,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一般说来,寻求真理的过程也就是去蔽的过程。但去蔽不单单意味着寻求、思考,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智力努力的过程。aleetheia更为准确的意思乃是“无蔽”或者说“敞亮”。正是在这一点上,aleetheia与sophia具有内在的关联。因为,sophia的词根为phoos,光。从而,sophia本真的意思乃是“一种光明”,凭借这种光明,sophia把自己展现为一个澄明之境,而这正是真理aleetheia“无蔽”、“敞亮”的内涵。所以,追求真理的人,也就是追求智慧的人,如前面毕达戈拉斯所说,“只有philosophos才追求aleetheia”。真理与智慧的这一内在关联表明,真理就是“无蔽状态”。这一本质性的界定告诉我们,寻求真理更重要的是能够立于、处于、置身于这一无蔽状态,而这就不单单是一个理智运思的过程,还蕴涵着意志的活动,它是意志的一个决断,通过这个决断,寻求真理的人把自己整个地置于真理之中,使自己本身作为“无蔽状态”展现出来。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说,真理内在地与自由相联。这是因为,唯有自由者能够处于无蔽之状态。而这是因为,唯有自由者才无所畏惧地解散了一切俗世的牵连,把自己完全地交付到了真理的手中。只是在这样彻底的决绝之中,一个无蔽状态准备好了,而真理的隆隆雷声开始在天宇震响,在人心中激起感应。这非大无畏者不能办,但另一方面非深于爱者又不能无畏。只是这样,哲学才最终把自己与爱牵连在一起。这是对真理至深的爱,它把自己投向真理无蔽之状态(philosophia),在这里静等智慧之光破晓的透亮。这样看来,哲学作为对真理和智慧的寻求,在其本性上乃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向来不在自由之中,我们为世虑所纠缠,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在许多方面我们是奴性的,从而问题首先在于我们能不能自由,敢不敢自由?我们能否象打鱼的载伯德的两个儿子把自己坦然交付给耶稣一样[2],把我们自己交付在真理手中?尼采在《看哪,这人》中这样写道:“凡是善于发现我的著作散发出来的气息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一种高空之气,振奋之气。人们必须对它有所准备,不然,一旦身处其中就有非同小可的受寒危险。寒冰在近,孤寂无边,——然而,躺卧在阳光下的万物是多么沉静!呼吸是何等地自由自在!人们会感到有无数的事物处于其间!正如我一向认为和经历的那样,哲学甘愿生活在冰雪和高山——在生命中搜寻一切陌生的和可疑的事物,搜寻以往惨遭道德禁锢的一切。”[3](p.5)实际上,人们长久以来所禁锢的不是别的什么,就是真理和自由。所以,真理和自由是危险的。但正因此,它激发起至深的爱与大无畏。危险、深爱与无畏成就了哲学。这样看来,自由乃是哲学的前提。自由与sophia,aleetheia,philosophia,philosophos的这样一种内在关联,是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基本洞见。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谈到哲学时明确地说“诸知识中唯有它是自由的”(982b27),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谈及古代哲学家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时又这样说:“他们对自身得益之事并无所知,而他们所知的东西都是罕见的、深奥的、非人之所能及的,但却没有实用价值。因为,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对人有益的东西。”(1141b6-10)在这样一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上,他进而把哲学与自由的一个独特的境域——闲暇skholee联系在一起。他这样说:“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都已具备的时候,在那些人们有了闲暇的地方,那些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才首先被发现。由此,在埃及地区,数学技术首先形成,在那里,僧侣等级被允许有闲暇。”(981b21-26) 这样,skholee就被展现为哲学活动发生的具体的、基础性的自由之境域。那么,何谓skholee?闲暇并非无所事事。在古希腊skholee并不意味着怠惰和静止,相反,skholee是与积极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作为“闲暇”的skholee,它的一个基本的转义就是指“占用了闲暇之事”。可见,skholee并不意味着空洞、空虚,它为事情所占用。但何谓“占用了闲暇之事”呢?岂不是一切工作都在占用着我们原本空闲的生命吗?而我们也了解在现代生活中的所谓休闲是什么。它是一种消费行为,为市场所操纵。市场不仅操纵着我们怎样工作,也操纵着我们怎样休息、娱乐。在市场的操纵下,我们积极地投身于健身、旅游、餐饮、购物、娱乐、社交。在此,我们非但没有进入一个自由之境,相反,却更深地陷入了俗世的缠绕之中。从而,在如此的闲暇之中,我们非但没有成为空洞,相反却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占用,以至于忙得不亦乐乎。这样看来,askholia“忙碌”不正是skholee的实现吗?由此,skholee竟然在其相反的意义askholia中消失了吗?那么也就无所谓闲暇了?!skholee即askholia,askholia即skholee,askholia之a—也就没有否定的意味了,从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样一段话“人的本性谋求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忙碌(askholein),而且是能够安然享有闲暇(skholazein)。……skholee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假如两者都是必需的,那么skholee也比askholia更为可取,并是后者的目的,……”(1337b30-34)也就毫无意义,全是空话了。如此一来,我们还怎么能够理解与自由之思想相联的skholee呢?但这只是想当然之推论。在古希腊,skholee并非指占据我们生命的一切事情。对古希腊人来说,那能够“占用闲暇”的是一类特定的事情,这就是言谈,尤其是指学术性的讨论、辩论和演讲。古希腊人把skholee之名赋予这样一类事情,认为它们在本质上属于闲暇。这样,skholee的积极有为,并不使它走到它的反面askholia“忙碌”之中去。占用闲暇的是一些自由之事,它使我们的生命充实,而不是陷入到无谓的忙碌之中。由此,它持久地占有了闲暇,保有了闲暇作为自由之境的本质,并将这本质真正地实现了出来。 由skholee“闲暇”的这样一层转义进而引申出另外一重意义,即“度过闲暇之地”,拉丁化后成为schola。西方教育中一个基本的词school即由此而来。从而,school在本义就是“度过闲暇之地”。school的本质就是自由。而我们知道,school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学派。从而,哲学正是在闲暇之中发生,它具有闲暇的本质,这就是说,它是自由的,并且在一个提供了自由之保障的地方发生。由此,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这样说:“作为思辨的理智的现实活动看起来正是以闲暇来区分的,……它在自身之外别无目的可追求,有着本己的快乐……以及属人的自足、闲暇和孜孜不倦。”(1177b19-22)。 二但是,skholee只为哲学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境域。人们占用闲暇之事颇多,从而享有闲暇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从事哲学思考。这样,我们还必须询问,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一个自由人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一次深长的思之中去了?我们说,这就是惊奇,古希腊语写作thauma。惊奇开启了哲思。柏拉图说:“thauma原是哲学家的标志,此外哲学别无开端。”[4](p42)这里,“开端”一词是arkhee,海德格尔因此在《什么是哲学》中发挥道:“惊奇是arkhee—它贯通于哲学的每一个步骤中。”[5](p603)而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阐述则更为详细。他这样说:“无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考(philosophein)的,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例如关于月象的变化,关于太阳和星辰的变化,以及关于万物的生成。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便自觉其无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爱智慧的人也就是爱奥秘的人,奥秘由可惊之物构成)。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任何实用为目的。当前的事情自身就可作证,可以说,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齐备之后,人们为了娱乐和消遣才开始进行这样的思考。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982b12-28) 在这段话中,除了论述到哲学解散一切俗世牵连的自由本性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把惊奇(thauma)树立为哲学思考(pilosphein)的开端。但这不是一种泛泛的哲学思考,例如就不是一种学究式的、以职业方式进行的思考,在这个思考过程中是没有丝毫惊奇可言的,而是充满了教条和程式,触处皆是已死之物。在这里我们应当对pilosophein一词思考得更深一些、更为本原一些。它毋宁说是一种“哲思”,而作为哲思,它摆脱了一切成见和固有的模式,把自己展现为一种纯思,一种解放了的、自由了的思,它仅为对真理的爱和渴求所贯注。而每个人只是在他对世界表示出最原始的惊奇的一刻,才最有可能具有这种“哲思”。此时,他摆脱了一切思维的矫饰和麻木,不再羞愧于自己的无知与迷茫。他开始象儿童一样地提问,并试图结结巴巴地去言说世界和自身,所问的是关于生活、关于世界的最为基本的问题,而不是一些高深的问题。从而它是笨拙的,但它甘愿笨拙;它自觉到自己的无知,并为自己的无知感到震惊;它为问题所缠绕,不掩饰这种无知,不逃避这些问题,而是勇敢地置身于其中,在茫然无知之境展开艰苦卓绝的思考。但由此它也就开启了对事物最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因为理解和认识总在惊奇与困惑之中发生。这样看来,正是惊奇把我们置入了哲学思考之中,哲思于惊奇之中现身。惊奇就仿佛是一道光明,思想为它所启明。因此,为了更为深刻地体悟哲学之思及其发生,我们有必要来对惊奇作一番细致的分析。我们首先注意到,惊奇毫无疑问是一种情绪,但它是一种独特的情绪,对它我们不能说,“让我们惊奇一下吧”,“让我们以此消遣一下吧”,不,这还不是真的惊奇。真的惊奇到来时没有丝毫的征兆,我们也许在路上匆匆地行走,也许在低头工作,为生活所困扰,但只是不经意的一抬眼,我们惊奇了,我们一下子被它攫住,整个身心为之震动,仿佛为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所吸引,我们从疲倦我们身心的繁忙的日常事务中挣脱出来,处于一种恍然自失的状态。惊奇到来之时,世界变得无限深邃而辽阔,万物放出安详而静谧的光芒;惊奇过去之后,世界依然故我,我们发现生活还是老样子。但是从此内心为一种神秘的光所照耀,我们懂得,我们的生命是属灵的。因此,我们不能用日常的眼光来看待惊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缺乏可惊奇的东西,因为日常生活中虽然充斥着惯常的事物,但是人们也时时要弄出一些新奇的事物来,以给生活一些小刺激、小惊喜,使贫乏的时代也有属于自己可夸耀的东西。但惊奇并不是对新奇事物的惊奇,这,常人们也会,而且更善于大惊小怪。这样的惊奇只是眩惑而已,我们被事物所传递给我们的新奇的官能刺激所吸引,沉迷于其中,偶或有一问,但很快我们便“懒得去想”了,它并不开启人的思想,相反却使我们远离思想。真正的惊奇不仅仅是对事物的新奇感到惊奇,而更多地是对事物的惯常感到惊奇。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这样描绘惊奇说:“无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考(philosophein)的,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例如关于月相的变化,关于太阳和星辰的变化……。”在这句话中,我们要注意的是taprokheira“身边的东西”这个词,它由pro“靠近”和kheira“手”构成,因此直译就是“手头之物”。显然作为手头之物,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实用性和日常性,它是我们日常经验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在反复的操持中,我们的手变得富有技巧,思想却沉睡了。但亚里士多德指出,真正的惊奇正发生于此,而由此出发,我们才可能触及到更为重大的问题。因此惊奇在本质上不只是对新奇事物的惊奇,反倒是对日常事物的惊奇。我们惊奇于它为什么要以这样一种熟识的方式存在,因为它完全可以有另外的存在。这样,经验知识的现成性和完满性就被打破了,事物的存在被动摇了,一种解放的力量被唤醒,人们仿佛窥探到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在这里充满了不确定,从而无知感产生了。(亚里士多德说:“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便自觉其无知”。)于是,惊奇就唤醒了一种沉思的力量,它把我们引向事物的存在本身,或者说让事物作为其自身而展现,它由此就敞开了一个崭新的境域。而这就是哲学之自由的境域。这样看来,惊奇是一种真正思想性的力量。惊奇就是思想,思想就是惊奇。自然,它无疑是一种情绪,一种欲望,但却是一种纯粹的欲望,一种“思”之欲求。这就是说,它作为欲望,排除了任何功利性的目的,脱离了一切物欲,而仅仅“想”知其究竟。这样,这种纯粹的“思”欲就把心灵从其正在从事的实际事务中,从俗世的牵连中推了出去,仿佛遭受了重重的一击一样,我们说惊奇的人丧魂失魄了。从而,惊奇就表现为日常实践活动的中断,它把人从日常生活中生拽了出去,使其突然置身于一个纯粹的思想的境域。惊奇就是这样一种伟力或奥力,而哲学就是它的奥迹。我们说,唯有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能够进行哲学思考,但这还不够确切,还应该说,唯有一个自由并能惊奇的人才能进行哲学思考。哲学要求一颗质朴无华的心灵,只有这样,它才能被惊奇所打动,并听命于它。不能摆脱虚荣的心灵与惊奇无缘;不能敬畏崇高与神圣的心灵也不能够惊奇。唯有兼具这二者,当惊奇来临之时,才能持久地、深长地沉入思之中。
但这样的思是怎样的一种思呢?我们前面说过,这是一种哲思(philosophein)。但什么是哲思?我们知道,这不过就是哲学philosophia。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作为最高的知识,被赋予了一个崇高的名称——theooretikee,思辨科学。但什么是思辨科学?思辨科学也就是理论科学,因为,theooretikee拉丁化后就写作theory,理论。但理论已经使哲学成为灰色的了,因此我们要从别的地方来寻找哲思的原初而本真的意蕴。我们知道,在古希腊语中,theooretikee由名词theooria而来,theooria意即“思辨”。而theooria又由动词theoorein而来。theoorein由theos和horan构成。theos意为“神”,horan意为“观看”。因此,“思辨”在其本义上意谓“神的观看”或者“神思”。theooria的这样一层内涵,在另一个拉丁语源的词contemplate中还保存着。contemplate译为“静观”、“沉思”,其词根temple即是属神的。把“思辨”解作“神思”是有根据的。因为在不止一处,亚里士多德都明确地强调,完全自足的思辨活动只有神才具有,唯有神才享有这一至福,而人只不过是分享了这一幸福而已。从“神的观看”中我们就瞥见了哲思或思辨最为原初的意蕴,它原来不是什么深邃幽缈之物,而就是纯粹的静观,它源于我们“看”的本性。这样无怪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以这样一句不同凡响的话作为开端:pantesanthroopitoueidenaloregontaiphusei。通常这句话被译作“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把它独特地解作“看的牵挂从根本上就属于人的存在”[6](p.52)。追究起来,这里作为“知”解的eidenai按其本义确实是“看”的意思,因为eidenai是horan的完成体的不定式形式。这样看来,哲思其最为原初的形式乃是观看,思之本性蕴含在看之中。但这是一种怎样的看?我们说,这是一种纯粹的看。亚里士多德正确地指出了 这一点。他紧接着上面那句话这样说:“人们甚至离开实用而喜爱感觉本身,喜爱视觉尤胜于其他。不仅是在实际活动中,就在并不打算做什么的时候,正如人们所说,和其他相比,我们也更愿意观看。这是由于,它最能使我们识别事物,并揭示各种各样的差别。”(980a23-26)这样看来,我们不是在别的观看中,例如就不是在动物猎食般地追名逐利的观看活动中进入沉思,而是在一种被解放了的、成为自由的看之中。只是在这样一看中,不仅我们,而且万物都从它们惯常的联系中、从它们世俗的价值中摆脱了出来,显示出自己本真的面目。而这样获得的成果就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正确地称之为idea和eidos。它们正是由horan的过去式的词根id而来的。从而,它们在本义上乃是视觉之形象。但既然我们这里所说的观看已不是日常的观看,而是纯粹的看,是神圣的观看,从而如此获得的视觉之形象就洗去了日常生活敷于其上的尘垢,而成为通体透亮的一种光辉的形象,成为事物之本真的面目。作为一种光辉的形象,它们就把自己展现为真理和智慧的无蔽状态、澄明之境。因此,柏拉图在指出惊奇是哲学的开端之后,满蕴深意地这样说:“说iris是thauma之女,并无误溯其血统。”[4](p.42)这里,所谓iris是指彩虹,人格化后为虹之女神,是宙斯的信使,向人传达神的旨意与福音。iris让我们同样联想到了看,因为作为天边的彩虹,荷马早已经把她与看联系在一起,称作thauma idesthai“奇观”。因而柏拉图在这里说“iris是thauma之女”显然含有看出于惊奇的意思。但这一看不是其他,它看到的是来自神界的消息,而我们知道,神界是远离世俗的,从而由惊奇而生的看,无疑是一种纯粹的看,这一看就把存在之真理本真地展现了出来。这样看来,哲学就是一种纯粹的静观,它立身于自由之境域,由惊奇而发生。在其注目之下,万物脱去了种种俗世的牵连,而复归于永恒的太一流行之中。由此,它把自己展现为一种真正解放性的力量。"
此段引自网上http://zhongjian.net/cgi-bin/topic.cgi?forum=26&topic=743&changemode=1聂敏里的文章。《什么是philosophia?》
在这里,聂敏里对philosophia(即译爱智慧)一词,有着明透的解释。这就是我们现所说的“哲学”一词的来源。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没有哲学一词的。也就是说,哲学一词是将希腊文中philosophia爱智慧翻译成中文时,而来的。那么将古希腊的philosophia一词翻译成中国文字时,为什么翻成哲学呢?
我认为:中国的文字,有些字的字意解释是可连带着与之相关连的另些字之意而用释的,是有相互借用之意的。如哲学的哲字,与晰(zhe)字通,而晰是明亮之意。又与遮字通,而遮是遮掩,遮蔽,即被掩蔽而难以看见之意。哲又与折字通,而折有翻转,反复之意。有折射,折服等引伸之意。哲又与辙通,而辙字,乃车轮压出的痕迹之意。故而哲学的哲字,在中国文字中所表达的含义有通过观察、认识事物的现象而折射出其中的道理,通过人的翻转,反复认识被掩蔽了的,而难以看见事物之理,从事物的运行现象等痕迹中找出规律。而哲学的学,是学说,学问之意。而学说,学问有系统之意。
我认为这就是哲学一词从字面解释的含义。
我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思想学说中,对万事万物的认识与看法,大多是从事物的道理上加以认识的。中国的易经就有理、象、术之论。而理,就是以现代所说的哲学部份。象是讲事物的现象,术则是具体方法。故而在中国古时,没有哲学一词,或这一说法,而称为理学。中国传统的理学思想也大多寓于在经、史著作与文学作品中,而没有专门的著作。如有也仅是经书而已。难怪西方人说中国是无哲学。而哲学一词是从西方此类学术著作中,将philosophia一词翻译过来的。
而在现在,由于百年来,西方文化近入中国后,其哲学一词也逐渐替代了理学。而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现在的人们对于这门学问,已没人在用理学一词了,而均在用哲学一词。
那么什么是哲学呢?哲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呢?哲学是讲天地间事物的最普遍性规律的学问。,它对事物的认识是基于不同的各种事物以及万事万物的不同具体的特性之上,将各种不同特性属性的具体事物,归纳、总结到所具有共同的特性与属性的层面上来认识的,故而它也是对事物最普遍性规律认识的学问。
哲学是由认识论与方法论组成。而哲学的认识论是指对天地间事物最普遍性规律的认识,它是对具体事物的运动变化规律,不断地抽象,提炼,最后归纳到事物最普遍性存在规律,最基本的属性的范围来认识的。而方法论呢?是在哲学认识论基础上产生的运用方法。
参考资料:http://www.chinathink.net/forum/printpage.asp?BoardID=3095&ID=20125
这就是哲学。
需要指明的两点是:
哲学 不等于 政治:哲学与政治不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更加不存在哲学附属于政治的说法。哲学独立于一切科学门类。
哲学 不等于 马克思主义: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总会误认为哲学无非就是马克思主义,其实不然,马克思只是哲学几千年发展中的外国哲学的一个小分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我们的政治发展方向,人们会产生这种错误观点。
哲学家可能对每一个问题提出很多种答案,但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思考的过程本身。
哲学思考又与语言紧密相关,哲学不是文学,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它要求用最清晰简练的语言去表达思想。
哲学问“为什么”,“怎么做”不是它关心的问题。哲学家都会认为,理论比实践要难得多。
依我的的看法,哲学就是思想,它是哲学家的独特的思想,把这种思想用逻辑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成的理论体系就是哲学。哲学就是不同的哲学家云自己的思想观点对世界和人生所作的解释。
什么是哲学?如何理解!
1、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 2、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3、哲学是方法论和世界观的统一 4、哲学是对其他具体科学(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思维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对哲学的理解:1、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当中 2、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 3、哲学是一门给人智慧...
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哲学?(1)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2)哲学的特点:抽象性和普遍性。(3)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区别:对象不同。哲学的对象是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一般或普遍规律。具体科...
哲学是什么意思?
哲学的名词解释:1、哲学:世界观的理论形态,或者说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2、世界观: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看法、根本观点。3、方法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方法论与世界观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4、哲学基本问题:存在和思维、物质和...
哲学是什么意思
哲学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类研究世界的基本学科和手段。从历史的角度看,哲学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什么是哲学 论文
1、什么是哲学: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与理论体系。 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和世界关系的根本看法。 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则与方法。 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于思维主体的思维过程;统一于思维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践过程;统一于主客体作用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发展过程。 2、哲学与一般...
哲学是什么?什么是哲学?
哲学,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形式,以认识、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为研究内容的科学。 同时,在...
什么叫哲学?都包括哪些方面?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世界观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发展的根本规律、人的思维与存在的根本关系的认识,方法论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方法论是世界观的功能,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主体与客体(包括思维与...
什么是哲学
1、一般性的,也就是从哲学的本质来说,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具体知识的概括和总结。2、从哲学的字义来说,哲学是一种使人聪明、启发智慧、追求智慧的学问。3、从哲学和世界观的关系来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4、从哲学和方法论的关系来说,哲学是关于方法论的学说。5、从哲学和世界...
什么是哲学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所谓世界观,是人们对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人人都有世界观,但不能说人人都有哲学。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属于哲学范畴,二者是相对立的。一分为二属于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又...
什么是哲学 及其含义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形式,以确立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社会科学。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意即“热爱智慧”。社会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