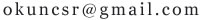分析她的小说特色和她独特的人生观,具有很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中以下三点表现尤为明显。
一、 人物形象的悲剧美学体现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在学生时代的张爱玲这样描述生活的本质。
中国对于悲剧人物的一般理解是,自身相当完美的人物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是因为邪恶势力的迫害,因而遭致失败甚至毁灭,如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这些说法概括起来就是——好人受害是因为坏人作恶的结果,我们也总是以这样的视角去分析具体的悲剧人物形象。
这种悲剧类型在张爱玲小说最典型的就是《十八春》,沈世钧、顾曼桢二人的爱情悲剧是由顾曼璐、祝鸿才的陷害造成的。“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时间,这几年里面却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仿佛把生老病死一起的哀乐都经历过了。”的确,在张爱玲的笔下,故事总那么地奇曲,总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本来认为,世钧和蔓桢会如同所有旧上海的男女一样,相识,相恋,结婚,生子,一同走过艰苦的岁月。但是,张爱玲的小说没那么平凡,在蔓桢与世钧已经到谈婚论嫁的时候,蔓桢的姐姐出现了,他们夫妇心生毒计,故事从此变了。蔓桢从一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单纯少女,一个坚强的自力更生的职业女性一下变成了莫名的受害者,在身体和精神遭受巨大的打击折磨之后,她对爱情的憧憬,对生活的热情化为乌有。只有张爱玲这样的“旷世奇才”才会安排这样的悲剧情节。
曼桢不是绝世佳人,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上海小户人家的女儿:旧象牙色的肌肤,鹅蛋脸,永远沉住一洼微笑的黑的眼。将来嫁了人也许会发胖,渐渐变得开了后门与弄堂菜贩扯着喉咙争青菜茭白价钱。这样的两个人,他们再爱都是平平淡淡的家常琐事,温和如一锅煤炉上炖着的细白小米粥,好莱坞的浓情电影模式不属于他们。让人感动叹息的地方是他们爱情的悲剧性,得不到的才珍贵!那样平凡的感情,只有化为悲剧才会有赏鉴的价值。试想世钧与曼桢如果真的一帆风顺的结了婚,反而无趣。婚前那一点薄弱的感情基础很快就在柴米油盐醋茶中消磨殆尽,永远为着无数的鸡毛蒜皮事件呕气,过个三四十年,照旧是白头偕老,沦为无数普通家庭中一员。张爱玲深谙大众心理,一支笔轻轻将他们隔开,让他们彼此对对方留住一点情,埋在心底藏起来,留作将来相见的余地。后来他们经历了那么多年那么多事,终于重逢,曼桢把两人分开后她的遭遇,掺着无限的苦痛,讲给他听:
“那时候一直想着有朝一日见到世钧,要把这些事情全告诉他,也曾经屡次在梦中告诉他过,做到那样的梦,每回都是哭醒了的,醒来还是呜呜咽咽地流眼泪。现在她真的在这儿讲给他听了,却是用最平淡的口吻,因为已经是那么些年前的事了。”
世钧默默地听着。
“他们很久很久没有说话。这许多年来他们觉得困惑与痛苦的那些事情,现在终于知道了内中的真相,但是到了现在这时候,知道与不知道也没有多大分别了——不过——对于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分别,至少她现在知道,他那时候是一心一意爱着她的,他也知道她对他是一心一意的,就也感到一种凄凉的满足。”
张爱玲自觉地以情欲、以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假如不是被情欲或是虚荣心所欺瞒,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这一点: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柯尔说过:“所有伟大的悲剧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二、 关注旧时代妇女的生存空间及生存方式
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表现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她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难以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她笔下女性形象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有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的缺陷性。
《半生缘》中的曼璐,开篇就写她年纪轻轻就独立支撑起养活祖母、母亲和弟妹的重担,作为一名弱女子她是无法承担这样的家庭重担的,她只有去做舞女和暗娼,用青春和美丽作为生活的唯一成本。但随着作者对她逐渐膨胀起来的人性深处的恶的展示,“我们无法不怀疑她这一行为的背后,有多少是为家庭为亲人作出牺牲的成分,有多少是自己贪图享乐、禁不起诱惑的成分,甚至她为家庭和亲人付出牺牲也可以成为她自甘堕落的借口,一种摆脱心理焦虑的伪饰”。话虽是偏激了点,但却是对曼璐这一人物形象的绝好理解。像这样为了生计的女子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随手就可拈来:《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被称为情场上的赌徒和高级调情者,以神圣婚姻作谋生之道的实利者和庸俗者;《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带着黄金枷的性变态的定格典型;《连环套》中的霓喜则在出世的当时便成为“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中的不真实存在。
她们的身份——一为社会底层的小家庭女儿,一为破落世家的大户小姐,一为麻油店里的小家碧玉,一是粗俗荒蛮的广东乡下的下等养女——形成了明显的等级,命运、性情也毫无关系及雷同之处。但当我们撇开这些表面的区别,深入到更深一层时,我们却能在她们永远没有交点的各自命运的平行线中,嗅到某些类似的充满悲剧意味的气息——那就是,同是身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的女性——不管她是小姐亦或是丫环——同是生活在“已经在大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仓促的、充满恐慌的时代, 她们作为传统意义上毫无生存能力的个体,为了维持自身基本的生存,而不得不作出各种费尽心机、饱含苦痛的艰难努力。他们或借助机巧、或倚仗金钱、或凭靠肉体,方式不同,却都在为着同一个人类最原始的愿望——生存而苦苦挣扎。
张爱玲在描述种种女性生存方式的时候,最终指归都是一种最基本最实在的物质生活。不管是婚姻也罢、金钱也罢、肉欲也罢,其实都只是她们获取必要的物质倚靠以保障生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生计问题是如此迫切地摆在眼前,以至各种形式的爱及其它种种的精神生活,对张氏笔下的女性而言都是一件遥远的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张爱玲的这种实实在在的物质意识有她自身真切的身世之感,更是她对生活于乱世的“时代弃女”及其生存的一种独特体认和把握。
人们在给予那些被动地以婚姻为职业的女性过多的同情和悲悯的同时,却鄙夷地、冷酷地谴责如曼璐、流苏,称其为“女结婚员”,鄙视她们对婚姻的主动性。这种因态度的被动或主动的批评仍是一套高高在上的男性话语,他们对女性的生存进行着种种的道德评判和社会评判。这些女性多是被动地沦为生活的牺牲者,她们或沦为娼妓,或为哥哥换亲,或为婆家挣钱,或被丈夫典当,都无一例外地为了自己或他人的生存沦为了畸形婚姻中孤苦无告的悲剧典型。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说:“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当时的女性,在社会动乱、女子身份低下的情况,更渴望有所依附,首先是物质的、生存的,然后也怯怯地盼望着一丝爱的亮光。可就连与张爱玲同时红于上海滩的女作家苏青这样有才气有智识的女子,在谋生之外企图谋爱却也仍是失望,她在说“没有爱”的时候,“微笑的眼睛里有种藐视的风情”。女子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谋取生存,所以她们在发现没有爱的时候不敢有丝毫的藐视,她们必须紧紧地抓住周围可见的一切东西,“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三、 表现女性的生存价值取向
张爱玲被誉为“旷世才女”,她的作品被广泛流传,她的生平被看作另一个“传奇”。有人说张爱玲的作品就像从旧箱子里翻出来的散发着樟脑味的锦缎旗袍,它的陈旧和奢华如此对立又融通地并列着,或许吸引人的就是她编织的那个精致的海上繁华梦。 当时的女性更是被时代抛在一个危险而又无奈的边缘。
在《半生缘》中,突出表现了一个与当时世情不大相适宜的人物——顾曼桢。这个女子生活在繁华都市大上海,灯红酒绿,烟花翠柳应该是比较熟悉,更何况有一个在风月场卖笑的亲姐姐。如果要让生活来得更容易一些,自己也更随意一些,那么她的职业选择可以参照姐姐的。但是,顾曼桢的生活方向很坚定——依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和家人——绝不做男人的依附,更不可能成为男人的玩偶。她信心坚定,虽然对姐姐的事情了如指掌,但她一如既往地尊重姐姐,理解姐姐对家庭的付出,懂得姐姐的良苦用心,明白世事的艰难。
曼桢在姐姐结婚以后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不得不兼职,又托人找到一份打字的工作,觉得还是不行,又再兼职教书。三份工作对一个女孩子是很难的,即使没有太多的付出,单就三处奔波也是很劳累。由于世钧很爱曼桢,体谅她的难处,想为她分担,于是向曼桢求过三次婚,曼桢都给拒绝了,两次都是在曼桢的家里。难道她不爱他吗?
第一次:世钧道:“曼桢,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我上次回去,我母亲也说她希望我早点结婚。” 曼桢道:“不过我想,最好还是不要靠家里帮忙。” 世钧道:“可是这样等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曼桢道:“还是等等再说吧。现在我家里人也需要我。” 世钧听了很不高兴,认为结婚后两个人总比一个有办法。而曼桢不原意把世钧“拖进去”,道:“你的事业才正开始,负担一个家庭已经够麻烦的,再要是负担两个家庭,那简直就把你的前途毁了。”
第二次:曼桢去南京看望世钧,几个年轻人去清凉山玩回来,在世钧家的起坐间里,两人一面烤火,一面吃着煨荸荠,曼桢穿着世钧的“狗套头”,世钧“在口袋里摸了一会,拿出一样东西来,很腼腆的递到她面前”,原来是送她一颗通过自己打工挣来的钱买的红宝石粉做的戒指,男女之间送戒指,在当时的用意相当明显,就是求婚。曼桢高兴而且幸福地接受了,这颗戒指也成了他们俩两情相悦的唯一信物。
第三次:世钧已经从工厂辞职,要回南京照顾年迈多病的父母,他想方设法赶回上海,来把这些不得已告诉曼桢。世钧道:“还是早点结婚好,老这样下去,容易发生误会的。” 曼桢道:“我们不是早已决定了吗,说再等两年。”世钧道:“其实结了婚也是一样的,你不是照样可以做事吗?” 曼桢道:“那要是——要是有了小孩子呢?孩子一多,就不能出去做事了,就得你一个人负担这两份家里的开销。那还有什么前途?”
即使是在被姐姐姐夫暗算以后,曼桢一心也只想逃出去,再好的富贵繁华也留不住她。这里尽管有她对世钧的一片痴情,不依靠男人、追求自主的思想也很重要。曼璐在妹妹遭到自己和丈夫策划的“酒后失德”之后,带着说不清的感情来看受伤的妹妹,想劝说妹妹“依”了祝鸿才,曼桢劈手把桌上一只碗拿起来往地下一扔,碗也破了,她捡起一块锋利的瓷片,道:“你去告诉祝鸿才,他再来可得小心点,我有把刀在这。”当她从医院逃出去后,又找了教书的工作,母亲来劝她去做祝鸿才的姨太太,她照旧是态度坚定。即使在后面为了自己的孩子,也为了姐姐的遗愿,违心地与祝鸿才结婚,她也仍然坚持出去做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这样坚持自己的人生态度的女子确实少见,用自己学来的本事养活自己,绝不依赖男人。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在张爱玲的散文《谈女人》中,这样写道:“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可见,张爱玲是谴责男权社会的。书中处处有对人生无奈的讽刺与苦笑。如果当初曼桢没有自力更生的想法,只是想到结婚后就可以靠男人生活,减轻自己的负担,那么故事可能就不会如此的以悲剧情节发展,也正是自尊自强的曼桢在表现自己生存价值取向在男权社会发生悲剧的缘由。悲剧的背后,我们仿佛能听见张爱玲这位有着孤零身世的“旷世才女”冷丁丁的一粒粒笑声。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很好地体现出作者的人生观,那就是女性生存的艰难。在她的小说《封锁》中有这样一句重复了多遍的民谣:“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虽然这些女性并没有真正落到没钱过日子的地步,但作为一种存在的恐慌却一直在威胁着她们。她们大多处于两种生存状态之中:一是急于想成为人家的太太或姨太太甚至情妇,总之是想找一个生活的依靠;二是在成为太太之后,仍然在为自己的地位而努力奋斗着,或变本加厉地抓钱,或无可奈何地在平淡的生活中苦熬着。曼璐正是这样的人物形象,而曼桢却成了一个社会的叛逆者特别的典型。
实质上,读张爱玲的作品翻来覆去感叹的是同一种荒凉情绪,作品中表现的正是她这种独特的人生经验。“她是一位创造了一种独特风格的优秀的女作家。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但我认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的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
不论是《半生缘》、《金锁计》、《倾城之恋》、《沉香屑》,还是《传奇》、《流言》任何一部作品,张爱玲都仿佛站在人世的云霄间用她淡淡的眼神藐视着世间的悲欢离合、人情冷暖,让后人永远的去想念她的容颜、咀嚼她的思想。
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独创性和缺陷
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有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的缺陷性。 《半生缘》中的曼璐,开篇就写她年纪轻轻就独立支撑起养活祖母、母亲和弟妹的重担,作为一名弱女子她是无法承担这样的家庭重担的,她只有去做舞女和暗娼,用青春和美丽作为生活的唯一成本。但随着作者对她逐渐膨胀起来的人性深处的恶...
...结合具体作品谈谈对张爱玲小说鲜明艺术独创性的认识和理解。_百度...
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
张爱玲小说的思想主题是啥
以女性的笔触写世俗的人生百态,作品通过写各位女性主人公的故事,显示了在战乱、贫困等环境下的人生百态,女性面对人生困境的选择及喜怒哀乐。张爱玲的人物有深深的看透俗世但又融入俗世,有着刻意的理性,就如白流苏,张爱玲小说中的主角,往往努力洞悉世态人心,所以诸多冷峻。
张爱玲小说创作时所处的社会背景 社会环境 急急急
3.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以及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的缺陷。 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古典小说的根底"和"市井小说的色彩"。 张爱玲小说中的"古典小说的根底"最为鲜明的表现又在于她作品中的"《红楼梦》风",教材中以《金锁记》为例,说明作品中随处可见《红楼梦》的...
请以张爱玲小说为例,分析海派文学的特点。
张爱玲小说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主要表现为“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在教材中我们说,张爱玲小说中的许多主题、意象和象征都是古典小说和通俗小说所无法“拘限”的,因为她的创作中增加了外来的小说技巧或现代派的手法,在中国现代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这对似乎“相克”的艺术形式中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调子。在...
张爱玲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张爱玲是有才情的,她的才情表现在她的文字上,她的语言里。她是骄傲的、犀利的,但我认为并不是特别的强势。对于男人,她是爱的,但从不卑微。我读过她的文字,觉得她对于爱情的解读,在那个时代真的可谓是难得。她笔下的爱情有风花雪月的、有现实的、也有目的性的。而她本身对于爱情,应该还是...
张爱玲《金锁记》中:月亮,镜子以及屏风中的鸟,分别有什么含义?
二 意象的艺术意味(1) 意象与作者的经历意象手法的运用,同张爱玲人生经历中瞬间的感受和直觉乃至童年记忆、潜意识等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凭借着她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以及超乎常人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悟性,使张爱玲运用这一艺术手法时显得极其熟练而游刃有余,具有鲜明的独创性,我们还是能从中窥见张爱玲生活经历的...
现当代文学论文题目
9. 色彩、意象与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性 10. 朦胧诗与新生代诗比较论 11. 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宗教情怀 12. 从《受戒》看汪曾祺的佛教文化意识 13. 汪曾祺小说文体的独创性 14. 试论汪曾祺的传统性 15. 论张贤亮小说的女性情结 16. 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寻根”情结 17. 千古文人侠客梦—...
《风声》,一场高级版的“杀人游戏”
麦家的小说具有奇异的想象力和独创性,人物内心幽暗神秘,故事传奇曲折,充满悬念,多被改为影视作品。由他编剧的电视剧《暗算》和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声》是掀起中国当代谍战影视狂潮的开山之作,影响巨大。《风声》讲述的是1941年,发生在杭州西子湖畔一栋小楼里的“密室”游戏。五个军官,三男两女...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共有几次思潮?分别是什么?
诗学体系:强调主观性的艺术本质观、独创性的艺术生成观、自律性的艺术功能观;主题形态:人性复归、个性主题;传统渊源:人生哲学、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5、左翼文学思潮 基于革命形势,是革命乌托邦的想象方式,理论贡献有:新写实主义、唯物主义文艺观及方法理论、典型理论的引进和阐释。6、现代主义文学...